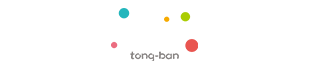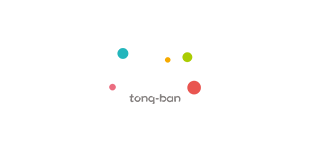什么是中国美学?这个问题似乎很难简明地回答。不过,回答什么是中国美学的问题,并不必然要撰写中国美学史或者建构中国美学体系。我们既可以通过撰写中国美学史或者建构中国美学体系来回答这个问题,也可以三言两语来回答它。甚至,某些撰写中国美学史或者建构中国美学体系的人,也并不一定能够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美学的轮廓,因而不能简明地回答什么是中国美学的问题。如果不是因为比较或者跨文化传播的需要,我们真有可能只是研究中国美学而不会提出什么是中国美学的问题,即只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中国美学,而无需确切地知道什么是中国美学。如果不拉开距离,对于自我的确就难以获得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对于艺术、审美这些高度依赖个人趣味和文化习惯的领域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一
对于中国美学的总体认识的困难,导致一些外国辞书中缺乏“中国美学”条目。比如,《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就没有收录“中国美学”,但收录了“日本美学”。撰写“日本美学”条目的作者帕克斯(G. Parkes)用物哀、侘寂、幽玄、粋、切等一组概念,就将日本美学的面貌清晰地勾勒出来了。我们能够仿照帕克斯用一组概念将中国美学的面貌勾勒出来吗?或者我们还有其他什么办法给出有关中国美学的核心信息吗?我们面临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一些重要的外国辞书中没有收录“中国美学”条目,不是因为辞书编撰者对于中国美学存有偏见,而是我们自己对于中国美学的研究不够深入,同时也是因为中国美学博大精深而不容易概括。
也有一些外国美学工具书收录了“中国美学”条目,比如库柏主编的《美学手册》就收录了“中国美学”条目,不过是与“日本美学”放在一起构成“中国和日本美学”条目。作者德沃斯金(K.Dewoskin)将该条目分①②③④Kenneth Dewoskin, “Chinese and Japanese Aesthetics”, in: DavidCooper ed., A Companion to Aesthetics,Oxford: Blackwell, 1997, pp. 68~73.
凯利(M. Kelly)主编的《美学百科全书》中有完整的“中国美学”条目。该条目分为三个部分,分别由三位作者完成。第一部分为“概述”,由苏源熙撰写。第二部分为“绘画理论与批评”,由卜寿珊撰写。第三部分为“中国当代美学”,由王斑撰写。三位作者都是美国知名的中国学研究专家。但是,遗憾的是,该条目没有对“中国美学”做出任何概括性描述。按常理,“概述”部分应该有一些概括性描述,但是苏源熙除了提醒注意不同艺术媒介之间的交替和哲学取向的变迁之外,就直接进入历史叙述了。苏源熙将中国美学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300年,大致相当于先秦两汉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公元300年至1400年,大致相当于魏晋南北朝至元朝时期。第三个阶段是1400年至1911年,相当于明清时期。第四个阶段是1911年至2000年,相当于现当代时期。对于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分期,苏源熙并没有做任何说明。(Haun Saussy, Susan Bush, Ban Wang, “Chinese Aesthetics”, in: MichaelKelly ed., Encyclopedia of Aesthetic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Vol. 1, pp. 44~60.)苏源熙将第一阶段命名为古风时期,主要讨论礼乐制度,尤其是乐论。最后讨论了汉代盛行的关联主义宇宙论,并试图用它来解释这个时期的乐论。苏源熙没有给第二个时期命名,只是描述性地将它称作“从‘清谈’到重建的古典主义”,主要讨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刘勰的《文心雕龙》和严羽的《沧浪诗话》,而对于小标题中的“重建的古典主义”这种说法,没有做任何解释。第三个阶段的标题为“重新评价日常性”,主要讨论明清小说及其理论,最后着重介绍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考》。第四个阶段的标题为“白话、大众和消费艺术”,讲到对西方小说的译介、白话文运动、木刻版画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光潜和李泽厚的美学、徐冰等人的当代艺术实践,等等。苏源熙为“中国美学”条目写的“概述”自始至终没有做出任何概括性的描述,对于尝试借助《美学百科全书》来了解中国美学的读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当然,苏源熙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来撰写“中国美学”条目的“概述”部分,与他的研究方法和文化观念不无关系。受到德里达和德曼的影响,苏源熙不是努力做出总括性的描述,而是相反,致力于解构固定的看法,包括由汉学家们构建起来的对“中国性”和“中国美学”的固定看法。在《中国美学问题》一书中,苏源熙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学术立场,他说:
本书一以贯之的观点是以修辞的分析性方法与下面的观念相较量:首先,一种特定文化的概要性统一;其次,一套形成概要性观点之基础的历史叙述;最后,历史问题绝对的——即哲学的——系统表述。([美]苏源熙:《中国美学问题》,卞东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页。)
苏源
与苏源熙不同,稻田龟男不反对概要性的系统表述,而且他在《东方美学理论绪论》一文中做出了相当成功的尝试。(Kenneth Inada, “A Theory of Oriental Aesthetics: A Prolegomeno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47, No. 2(Apr., 1997), pp. 117~131.)在稻田龟男看来,尽管我们今天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美学理论,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美学理论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和普遍性。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没有一种美学理论能够涵盖所有的领域。稻田龟男承认,他所说的东方美学理论,指的是融合佛家和道家思想的美学理论,这也是他与苏源熙不同的地方。苏源熙的研究多限于儒家的解释学传统,稻田龟男的研究偏重佛家和道家的形上学传统。如果说从儒家的角度来看,东西方美学的差距并没有那么明显的话,那么从佛家和道家的角度来看,东方美学的独特性是显而易见的。
在稻田龟男看来,东方美学的独特性基于东方形上学的独特性:“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佛家和道家形上学,这个词就是‘活力论’(dynamism)。”(Kenneth Inada, “A Theory of Oriental Aesthetics: A Prolegomeno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47, No. 2(Apr., 1997), p. 117.)换句话说,与西方形上学建立在“存在”的基础上不同,以佛家和道家为代表的东方形上学建立在“生成”的基础上,前者追求“永恒”,后者肯定“无常”。与专注于“存在”的西方形上学一味肯定“有”不同,专注于“生成”的东方形上学看重“有无相生”。
基于这种专注于“生成”的形上学,东方美学追求“有”与“无”、“秀”与“隐”之间的张力和动态平衡,这与西方美学单纯注重“有”和“秀”等可感觉的领域不同。就像刘勰所说的那样,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秀”是可感觉的领域,“隐”是不可感觉的或者说超越感觉的领域。“秀”与“隐”之间的张力,推动了审美经验的动态展开。与此相应,东方艺术体现出与西方艺术不同的美学追求。比如,以水墨画为代表的东方绘画,表面看起来像单色画,但是实际上水墨画中的黑白表达的是对色彩不持偏见,意味着可以替换为任何色彩。在稻田龟男看来,最能体现东方美学精神的是受到禅宗影响的艺术,特别是日本艺术。帕克斯在《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日本美学”条目中提到的那些范畴,被稻田龟男视为东方美学的代表。
尽管稻田龟男研究的领域是受佛家和道家影响的东方美学,因而没有将日本美学与中国美学区别开来,但是他从东方形上学与西方形上学的区别着手研究,试图从总体上揭示东方美学的特征,这种方法与苏源熙的解构主义解释学和修辞学的研究方法全然不同。就有效地给出“中国美学”的总体面貌来说,稻田龟男的研究方法似乎可以借鉴。
二
对于“中国美学”总体特征的把握,有不少中国美学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鉴于在这方面做出探索的中国学者较多,为了简明起见,我想以叶朗为例,梳理一下中国美学家在这方面的思考。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叶朗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流行观点做了梳理和批判性的分析,他重点分析了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西方美学重“再现”、重模仿,所以发展了典型的理论;中国美学重“表现”、重抒情,所以发展了意境的理论。
第二种看法:西方美学偏于哲学认识论,侧重“美”“真”统一,中国美学偏于伦理学,侧重“美”“善”统一。
第三种看法:西方美学偏于理论形态,具有分析性和系统性,而中国美学则偏于经验形态,大多是随感式的、印象式的、即兴式的,带有直观性和经验性。(关于这三种流行看法的批判性分析,参见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16页。)
在叶朗看来,这三种流行的看法都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叶朗提议,对于中国美学,应该先做深入的研究,后做总体的概括,而不是相反。尽管在撰写《中国美学史大纲》的时候,叶朗倾向于不对中国美学做总体性概括,但是他的一些总体性认识对于后来的中国美学史研究仍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比如,在研究对象上,他认为应该以“意象”为中心,而不是以“美”为中心。“在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美’并不是中心范畴,也不是最高层次的范畴。‘美’这个范畴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地位远不如在西方美学中那样重要。如果仅仅抓住‘美’字来研究中国美学史,或者以‘美’这个范畴为中心来研究中国美学史,那么一部中国美学史就将变得十分单调、贫乏,索然无味。”(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页。)叶朗的这种认识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非常重要。在我看来,正因为有了这种明确的认识,他的中国美学史研究和写作才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而且其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叶朗对于中国美学的认识,对于顾彬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顾彬说:
1994年我有机会到北京大学进行三个月的访学,有机会跟叶教授见面,他告诉我不应该从美来看中国文学,应该从意象、境界来看,这完全有道理。这不是说我不能用西方的方法来分析中国文学,但是如果我们也能够同时从中国美学来做研究工作的话,那显然就能够加深中国文学作品的深邃和深度。所以我们需要中国的学者发现并指出我们的问题所在。叶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得非常具体。所以叶朗丰富了我对中国文学的印象,我从1994年开始在他的影响之下写了《中国文学史》。(顾彬、李雪涛:《中国对于西方的意义——顾彬、李雪涛谈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中华读书报》2009年12月2日。)
在1988年出版的《现代美学体系》中,叶朗尝试将“意象”和“感兴”这样的中国美学概念运用到现代美学理论的建构之中,实现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融合和对话。同时,叶朗也意识到从文化大风格上来总结中国文化的审美特征的重要性,将受儒家影响的文化的审美特征总结为“中和”,将受道家影响的文化审美特征总结为“玄妙”,与西方美学中的“优美”和“崇高”形成对照。
到2009年《美学原理》出版的时候,叶朗对中国美学的特征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明确提出了“美在意象”的主张。“美在意象”的主张,不仅很好地支持了稻田龟男所说的东方“活力论”,而且与西方根深蒂固的主客二分架构拉开距离。我们说叶朗的观点很好地支持了东方“活力论”,是因为“意象”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动态生成之中;说他的观点挑战主客二分的架构,是因为“意象”既不属于“心”,也不属于“物”,在西方主客二分的形上学框架中找不到“意象”的位置。借用庞朴的术语来说,“意象”属于“形而中”,与它相对的是属于“形而上”的“道”和属于“形而下”的“器”。(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3~82页。另见彭锋:《美在意象——叶朗教授访谈》,《文艺研究》2010年第4期。)
在《美学原理》中,叶朗不仅对“意象”的本体论地位有了清晰的认识,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审美大风格的认识也有了推进。在《现代美学体系》中,叶朗用儒家的“中和”和道家的“玄妙”来对应希腊的“优美”和希伯来的“崇高”。到了《美学原理》,叶朗尝试用“沉郁”“飘逸”“空灵”来总结中国文化的大风格,将它们分别对应于儒家、道家和禅宗。叶朗指出:“在中国文化史上,受儒、道、释三家影响,也发育了若干在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审美意象群,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形态(大风格),从而结晶成独特的审美范畴。例如,‘沉郁’概括了以儒家文化为内涵、以杜甫为代表的审美意象的大风格,‘飘逸’概括了以道家文化为内涵、以李白为代表的审美意象的大风格,‘空灵’则概括了以禅宗文化为内涵、以王维为代表的审美意象的大风格。”(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21页。)
中国美学家对于审美风格的区分非常细腻,有关概念众多,比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中就列出了二十四个概念,与此类似的还有《二十四画品》《二十四书品》《溪山琴况》等,用来描述审美风格的概念数以百计。不过,叶朗认为:“这些概念多数还不能成为审美范畴,因为它们还称不上是文化大风格。”(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21页。)他之所以选出“沉郁”“飘逸”“空灵”三个概念作为中国审美范畴,原因是它们分别与儒、道、释三种思想文化紧密相关,因而是文化大风格。当然,至于审美范畴是否一定是文化大风格的结晶,这一点尚可商榷,尤其是在推崇多元文化和鼓励艺术创新的今天,究竟允许多少风格概念成为审美范畴,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不过,用“沉郁”“飘逸”“空灵”来取代之前的“中和”“玄妙”,已经可以看出叶朗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有了推进。这里的推进不仅体现在范畴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这些范畴与文艺实践的关系更加密切,尤其是与有代表性的诗人结合之后,能够让人对这些范畴的内涵有更加直观的理解。沿着叶朗的思路进一步研究,也许我们可以像帕克斯和稻田龟男用一组审美范畴概括出日本美学的特征那样,用一组审美范畴概括出中国美学的特征。
三
由于中国美学的博大精深,单纯用审美范畴来概括它的特征似乎有以偏概全之嫌。为此,我在给《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中国美学”条目的时候,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方式,结合前述《美学手册》和《美学百科全书》的特点,力图从中国美学独特的范畴体系、中国美学与哲学的关系、中国美学与艺术的关系以及中国美学的现代进程四个方面,勾勒出中国美学的面貌。
所谓中国美学,指的是以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为研究对象的美学分支学科,包括中国美学的范畴系统研究、中国美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研究以及中国美学与中国艺术的关系研究。
(一)中国美学的范畴体系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美学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范畴体系,集中表达了古代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意识。
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不是“美”,也不是“艺术”,而是“道”。“道”的特征是“自然”,与之相对的是具有“人为”特征的“技”。“道”与“技”、“自然”与“人为”之间的差异,不是实体上的差异,而是境界上的差异。任何一种事物,只要体现了“道”的特征,就都可以算得上是艺术作品。“道”与“技”之间的这种区别,与西方美学中的模仿与被模仿之间的区别完全不同。后者是实体上的区别,而不是境界上的区别。
中国美学描述审美对象的范畴是“象”,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意象”“意境”。“象”不同于西方古典美学中的形式美的概念,它不是指某种具有特殊形式的事物,而是指事物的一种特殊的显现样子。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比较接近现代现象学美学所讲的审美对象。“象”介于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器”之间,是一种既非观念又非物质的东西。“象”后来发展为“意象”,“意象”的基本特征是情景交融,是一种既非主观又非客观的东西。根据王夫之等人的认识,意象是主体与对象遭遇时所自然生成的样态,是事物向审美主体直接呈现的样子,同时也是事物最真实的样子。
中国美学描述审美经验的范畴是“兴”,后来发展为“感兴”。“兴”不同于西方美学中的“直觉”概念,它不是指主体一种特殊的认识事物的方式,而是指主体的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它既不同于主体用概念来理解事物,也不同于主体由欲念来对事物采取实践行为,中国美学常常把“感兴”状态称为主体的本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主体只是听凭自己的感受来同事物打交道,让事物在不受概念和目的局限的感觉中自由地显现。因此可以说,如果作为审美对象的“象”是事物的本来样子的话,那么作为审美经验的“兴”则是主体的本来样子。
中国美学还有一个特殊的范畴,既可以用来描述审美对象,也可以用来描述审美主体,那就是“气”。“气”是中国哲学中一个独特的范畴,它既可以指有形物质的一种基本元素,也可以指无形精神的一种可感形式,总之是某种介于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东西,精神和物质、主体与客体可以借此进行沟通和交流。中国古典美学的理想,就是试图以“气”为中介,冲破僵硬的物质外壳,达到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的更深层次上的交往与理解。
中国美学的核心问题不是发现形式美的规律或探讨艺术创作规律的问题,而是人生境界的问题。在审美境界中,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处于自由的交往之中,这里没有任何外在的限制却生成自然的条理和节奏,用儒家的话来说,这就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用道家的话来说,是“以天合天”的境界;用禅宗的话来说,是“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的境界。这是古代中国人理想的人生境界。
(二)中国美学与中国哲学
任何一种文化传统中的美学都要受到其哲学的影响,中国美学也不例外,中国哲学为中国美学提供了基本概念和思想方法。但与其他文化传统中的哲学对美学的单方面的影响关系不同,中国美学不仅从中国哲学那里借用基本概念和方法,而且反过来为中国哲学提供解释方式。这与中国哲学的特征有关。中国哲学并没有发展出严格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相反以人生境界为中心的人生论和价值论非常发达。中国哲学家在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也较少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而更多用比喻和象征等艺术表达方式。中国哲学之所以普遍地采取艺术的表达方式,与它所追求的目标有关。换句话说,中国哲学的目标决定了它只能以艺术或审美的方式才能实现;同时,由于中国哲学常常以艺术或审美的方式实现其目标,因此它所成就的人生境界也往往是审美的。
一般说来,中国哲学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不可言说”,甚至是“不可思议”。儒家所追求的“仁”、道家所追求的“道”和禅宗所追求的“第一义”都是不可以用概念直接言说的,只能用文学语言去暗示、象征,用体验去见证,这就是中国哲学普遍采用艺术和审美的表达方式的原因。所以儒家特别重视诗书礼乐,道家尽管表面上反对艺术形式,但实际上却蕴涵丰富的艺术精神,对中国古典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哲学所采取的艺术象征和审美体验的方式,决定它最终所实现的人生境界是审美境界。
总之,如果我们可以一般地说中国哲学追求的最高目标是“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的话,由于“天人合一”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因此用哲学思辨和逻辑推理的方式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目标,“天人合一”的目标只能在非思辨、非推理的(即超逻辑的)艺术表现和审美体验中实现;艺术表现和审美体验的方式,决定了“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只能是审美境界而不是哲学境界。这就是中国哲学与美学的内在关联。
(三)中国美学与中国艺术
中国艺术与追求本然人生境界的中国美学直接相关,由此鉴别艺术和非艺术的方式也不同于西方美学。与西方美学强调艺术和非艺术之间的区别是实体上的区别不同,中国美学强调艺术和非艺术之间的区别是境界上的区别,即“道”和“技”之间的区别。“道”的特征是“自然”,“技”的特征是“人为”,艺术就是使不自然的“技”还原为自然的“道”。只要一种“技”超越了作为人的活动所具有的各种局限,比如概念、功利目的和技术操作的局限等,“技”就从实用的层面上升到审美的层面,其产品也就由一般的人工制品上升为艺术作品。
由于中国古典艺术在根本上所要求的是一种自然的技艺(广而言之是一种自然的生活),其次才是这种由自然技艺所创造出的产品,这样中国古典美学事实上把什么是艺术品的问题超越了,而把问题归结为怎样才是艺术地生存。由此,中国古典美学特别强调一切艺术创作必须建立在“审美地存在”这一基础之上,因为中国艺术最终要保证的,正是人生在世的本然的存在状态,更明白地说,就是人生的艺术化。
由于艺术和非艺术之间是境界上的区别而不是实体上的区别,因此中国美学特别强调艺术家如何通过人格修养达到审美境界,而艺术技巧和艺术观念之类西方美学特别的问题倒在其次。反过来说,中国美学强调艺术在人格修养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现代性的观念,在中国美学中表现得很不纯粹。
(四)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进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受西方美学的影响,中国美学开始了它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的最初阶段表现为对西方现代美学的全面接受,其中王国维、蔡元培和朱光潜等人的早期美学思想最具代表性。比如,王国维根据西方美学的审美无利害性观念,批判中国历史上既没有纯粹的艺术也没有纯粹的美学,朱光潜最初建立起来的美学体系也只是西方现代美学观念的汇集。但随着美学研究的深入,传统美学逐渐得到重视,并对中国现代美学产生重要影响。如何处理西方现代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美学现代化走向深入发展时亟待处理的难题。总的看来,这些美学家在处理中西美学的矛盾问题上都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他们宁愿自己的美学体系出现矛盾,也不愿对中西美学做削足适履式的取舍。由于中国现代美学包容了与审美现代性相矛盾的传统美学思想,因此中国美学的现代性表现得很不纯粹。
随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的到来,中国美学开始寻找和研究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与西方美学展开交流和对话。随着对中国传统美学研究的深入,以及与西方美学的交流和对话的全面展开,中国美学将在世界美学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文心 诗情 博物 乐境
青少儿人文美育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