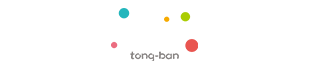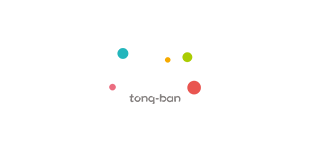作者简介:毛宣国,哲学博士,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12)。
内容提要:在中西美学和文论史上,“意象”范畴具有复杂的语义,西方美学和文论主要将“意象”作为一个心理学和文学的题目加以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范畴出现则与康德美学相关。中国古代美学则主要是从艺术和审美本体方面来认识“意象”范畴的价值,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周易》,但亦应注意到《周易》中所说的“立象以尽意”和“制器尚象”与作为审美意象的形象创构还具有一定的距离,不能简单将二者等同起来。意象与意境是一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能看成是一体两面、外在形态与内在境界和层次的关系。“意境”的妙谛不在象内而在“象外”,它是“以虚实为底相”的审美人生创造,是“意象”中最富于形而上的人生体验和审美追求的一种类型,并非情景交融,能创造意象的艺术作品都能达到“意境”的审美层次。朱志荣的“美是意象”说存在着“意象”与“审美意象”、“物象”与“心象”、感性形态与理性精神等方面的混淆,它主要不是从人与世界的存在关系和价值评判,而是从意象的感性形态以及人与世界所结成的对象性关系来看待“审美意象”的创构与生成。叶朗的“美在意象”说则不同,它虽然还存在一些逻辑概念的混淆和不严谨,但主要是从美与人生关系、美对于人生的意义方面看待“审美意象”的创构与生成,所以相比朱志荣的“美是意象”说,对于中国当代美的本体问题的思考更具有理论价值。

中国美学对“意象”理论的自觉关注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在这之前,“意象”概念亦在一些学者的美学和诗学著作中广泛使用。这种使用大致分两种情况,一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并没有清楚界定“意象”范畴的理论内涵与外延,如朱光潜在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写作的《谈美》《诗论》等著作中将“意象世界”与“美感的世界”“超现实的文艺世界”“诗的境界”中的“景”等同起来①,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讨论中,将“意象”与“物的形象”(物乙)等同起来,便是如此。二是将“意象”看成西方输入到中国的美学概念,并将它与英美意象主义(imagism)诗歌创作联系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敏泽在《文艺研究》1983年第3期发表的《中国古典意象论》一文,明确反对将“意象”看成是西方的舶来品,认为它是来源于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意象”范畴遂逐渐成为古代美学和文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同时,随着人们对中国传统美学与文学理论价值认识的深入,一种要求回归中国传统背景的美学与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受到人们的重视,于是出现了以中国古典美学“意象”范畴为核心的美学与文艺学体系的理论建构,如叶朗的“艺术本体”说(后来又用于解释“美的本体”,其代表说法是“美在意象”),汪裕雄的“审美心理基元”说,夏之放的“文艺学体系的基石”说,顾祖钊的意象、典型与意境的共同构成的艺术至境论,等等。最近又见到朱志荣的《审美意象的创构》和韩伟与之商榷的文章。朱志荣文章的基本观点早在2005年发表的《论审美意象的创构过程》②一文中就体现出来了,新近发表的论文有了进一步的充实与扩展。朱志荣的基本观点是将“意象”作为美的本体和基元范畴,而韩伟的观点则是反对将“意象”与“美的本体”等同起来。③这两篇文章观点差异很大,但都对美学范畴的“意象”作了较深入的辨析,对意象美学的研究在理论上有所推进。不过这种辨析与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进一步厘清与辨析的必要。因此笔者不揣冒昧,拟结合对朱文和韩文观点的辨析,对“意象”概念和以“意象”为核心的美的本体研究,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中西美学文论史上“意象”范畴的复杂语义
韩伟的文章批评朱志荣的关于审美意象的看法忽略了“意象”与“审美意象”的区别。他认为,在朱志荣的眼中,意象与审美意象是可以通约的,在行为过程中也未做出明确的区分。比如朱志荣所说的“所谓美即审美意象,指美是在动态审美活动中创构而生成的,是化生的,而不是预成的”,“平常所说的'美’,实际上是对象的形式潜质,与审美活动中主体以情感为中心的心理功能在想象力的作用下所创构的审美意象”,“物象经过感知、判断和创构而生成意象,即美”,“审美活动就是意象创构的活动,审美活动的过程就是意象创构的过程”,即是如此。按照韩伟的看法,审美意象应是意象范畴的子命题,而朱志荣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是将意象默认为审美意象。
不管韩伟的批评是否符合朱志荣观点的实际,他提出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回顾19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的“意象”理论研究,有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虽然“意象”范畴成为关注的对象,但对于什么是“意象”,什么是“审美意象”,在概念使用和理论界定方面是存在着很大的出入和模糊不清。另外,中西方美学与文论中的“意象”范畴的语义有什么不同,人们在讨论中常常也缺乏清晰的界定与区分。所以,要深入认识“意象”范畴的美学价值,首先应对“意象”范畴有清晰的理论界定,特别是应该注意区分不同文化、不同美学文论背景下的“意象”概念的语义差异,不能简单将中西方美学文论中的“意象”概念混同起来,也不能只要谈到“意象”,就认为它具有审美意义,简单地将“意象”与“审美意象”的范畴混同起来。
在西方美学文论中,与中国古代美学“意象”相对应的词语是“imagery”,它常常也和“image”(形象)、“icon”(语象)等词混用,是一个语义范围和指代对象较为模糊与含糊不清的术语。在西方,“意象”一词首先可以作为一个心理学术语看待。《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解释“意象”:“'意象’(imagery),人脑对事物的空间形象和大小的信息所作的加工和描绘。和知觉图像不同,意象是抽象的,与感觉机制无直接关系,精确性较差,但可塑性却较大。”[1]韦勒克和沃伦也认为“意象是一个既属于心理学,又属于文学研究的题目”[2]。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意象’一词表示有关过去的感受上、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与回忆,而这种重现和回忆未必一定是视觉上的”[3]。上述看法也说明,人们对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象”理解并不一致,一是强调“意象”抽象、非知觉性的特征,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看法;一是将“意象”看成在知觉基础上形成的,包含着对过去心理记忆的感性形象,如韦勒克和沃伦的看法。而从文学意义上说,“意象”可以看成是文学形象的一种类型,它首先是一种语言的事实,“是语言绘成的画面”[4]。“意象”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与文学理论的范畴在西方受到重视,与20世纪初出现的意象主义诗歌创作有着密切关系。意象主义诗歌不否认视觉经验,而是将视觉经验的呈现与复杂的心理事实紧密地联系起来。如意象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庞德就认为,意象不是一种图像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是一种“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④。韦勒克和沃伦赞成庞德的观点,认为“视觉的意象是一种感觉或者说知觉,但它也'代表了’、暗示了某种不可见的东西,某种'内在的’东西”,“意象可以作为一种'描述’存在,或者也可以作为一种隐喻存在”[5]。意象主义诗歌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庞德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爱好者,他重视的是意象的客体呈现,这种呈现方式与中国古代诗歌“托物寄兴”和“即景抒情”的意象表达方式有某种相似。但是,意象主义专注于一种神秘的诗歌经验和心理体验,将诗歌创作引向象征和隐喻的领域,又与中国古代诗歌的意象表现有很大不同。意象主义诗歌理论对“意象”的理解、对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不过,中国现代美学对“意象”的讨论与重视与这一理解则没有太多太直接的关系。
西方美学文论对“意象”的理解,若更早地溯源,还与“模仿”的语义和修辞批评传统相关。如周发祥先生所说的那样,“意象”一词,“在文艺复兴之前,这一术语仅仅指普通意义上的'影像’、'仿制品’或'复制品’,并不指诗歌中的艺术形象”,诗人运用意象创作诗歌,但并不自知,而是认为自己是在借助“修辞”进行思考。只是到了17世纪末,“意象”才作为填补语汇空白的术语,与想象、视觉经验一类关于诗歌创作的观念联系起来。[6]在西方美学中,“意象”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范畴的出现,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所表述的思想相关。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了“审美观念”( Idee)这一范畴。康德所说的“观念”(Idee),朱光潜和蒋孔阳先生均中译为“意象”。从康德的具体表述来看,“审美观念”虽然叫做观念,实际上是一种通过想象力创造出来的、能“生起许多思想而没有任何一特定思想,即一个概念能和它相切合,因此没有言语能够完全企及它,把它表达出来的”的感性形象[7],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意象”与“审美意象”十分相似,所以翻译成“意象”也是可以的。西方近现代美学一些理论家,或者将“意象”看成是“虚幻的对象”,认为“它的意义在于:我们并不用它作为我们索求某种有形的、实际的东西的向导,而是当作仅有直观属性与关联的统一整体”[8],或者将“意象”解释为“对象不在场但却有所呈现的某种方式”[9],亦与康德关于审美观念(审美意象)的理解颇为相近。这一理解,重视的是“意象”的虚幻、不在场,以有限的感性形式表现无限丰富的理性内容的特征,所以更具有审美本体的意味,与中国美学对“意象”范畴的理解也更为接近。
在中国美学中,“意象”的观念渊源最早可以上溯到《易传·系辞》:“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言以尽其言。”虽然这里所说的“意”是圣人所能体察的天意,“象”是符号化的卦象,与审美和文艺创作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是,把“象”作为一个能够达意的符号系统,肯定象以尽意、言以明象的功用,则对后世“意象”审美观念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将“意”与“象”联结为一个词,最早见于汉代王充的《论衡·乱龙篇》:“夫画布为熊麋之象,明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不过,这里所谓“意象”,是指具有某种实用性象征性的画面图像,与审美和文艺创作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最早把“意象”作为一个文艺和审美范畴提出来的是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提出“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的命题,这里所说的“意象”包含作家的心意和与这种心意结合着的物象的两方面内容,而且也充分肯定了艺术构思中的想象作用。如果再联系《神思篇》中“神用象通,情变所孕”、《隐秀篇》中“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等关于艺术构思、艺术语言与形象关系的表述来看,刘勰的确非常重视“审美意象”对于艺术创作的作用。“意象”一词在唐代则成为一个普遍使用的美学范畴。托名王昌龄的《诗格》说“诗有三格,一曰生思,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说“意象欲出,造化已奇”,张怀瓘《文字论》说“探彼意象,如此规模”,都是将“意象”作为美学范畴来使用。唐人还提出“兴象”的范畴,如殷璠“既多兴象,复备风骨”,皎然“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包含着艺术作品“意”与“象”,主体情思、客观物象与艺术表现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其实也是在谈“意象”。明清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意象理论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的理论,不仅将“意象”作为评价艺术作品的最重要标准,比如李东阳的“意象俱足,始为难得”(《怀麓堂诗话》),胡应麟的“古诗之妙,专求意象”(《诗薮》),王廷相的“言征实则寡余味也,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与郭阶夫学士论诗书》),而且抓住艺术创作的主客体关系、情景关系展开,将“意象”看成是主客一体、物我交融,情景相生的产物。比如何景明的“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与李空同论诗书》),王世贞的“要外足于象,而内足于意”(《于大夫集序》),王夫之的:“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姜斋诗话》),刘熙载的“诗或寓义于情而义愈至,或寓情于景而情愈深”(《艺概·诗概》)等等,均是如此。
中国古代美学关于“意象”的理解,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它与西方美学与文论不同,并不是将“意象”作为一个心理学和文学研究的题目,也并非像西方美学那样,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将它看成是与模仿的形象和修辞学的表现方法相关的,而是立于中国古代主客一体、物我交融、情景相合的哲学美学背景,充分意识到意象创造对于审美和艺术活动的本体意义。中国古代美学之所以少言“形象”而是重视意象和意象之美,主要在于中国古代美学始终意识到,所谓“意象”实际上是以“意”为主导的,是审美主体即景会心、以形写神的心灵创造。同时,中国古代美学也充分意识到,单有“意”的一方构成不了意象,意象的生成与创造,必须以“象”为载体,“象”在中国古代美学家眼中也不是对客观存在物象的简单摹仿,而是与“意”是不可分割的,处于审美主体意识观照中,在这种观照中呈现的。美的意蕴就体现在象与意、情与景、物与我、主体与客体有机统一与自然契合中。第二,虽然中国古代美学将“意象”作为一个基本的美学范畴,指向艺术和审美的本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人在使用“意象”和“象”的范畴时,不存在概念语义的混淆,也不意味着“象”“意象”一类概念的使用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审美意义。比如上文我们所说的《周易·系辞》“立象以尽意”和王充《论衡·乱龙篇》中的“意象”概念的使用,就不能简单等同于审美意义上的“意象”。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曾论及《易》象与《诗》的艺术形象表达的区别,认为易象是明理尽意的手段,理明意达之后,可以舍象,而诗则是“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10],“象”的创造本身就是目的,没有了象的表达,没有了意溶于象、象合于意的艺术创造,也就没有了诗。这种看法实际上也说明,审美意象,或者说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创造,是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的“观物取象”“制器尚象”的思维活动的,它是一种被诗意,或者说是被诗人主体情意所观照的事物,是心物交融、主客相契的“意中之象”,而且还要通过艺术化的媒介与手段展现出来。朱志荣认为,审美意象的创构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尚象精神,与《周易》的“立象尽意”“制器尚象”的思维方式相关,这样的看法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他说“立象尽意”也是审美意象创构的基本特征,甚至将《周易·系辞》中所说的“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韩非子·解老》中所说的“意想者皆谓之象”等等都看成是一种审美意象的创构活动,则失之简单化。他没有看到《周易》所说的“立象尽意”重在明理尽意,强调的是“象”可以达意、尽意的特点,对意象创造的“言不尽意”,以及意象创造中的主体情感因素和情与景的关系基本没有涉及,所谓“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意想者皆谓之象”等表述,也没有涉及主体创造情思的问题,与审美意象创构所呈现的基本特征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二、意象与意境的关系
朱志荣与韩伟的文章都涉及“意象”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审美意象与意境的关系。韩伟认为,朱志荣所说的“意象创构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便是产生虚实相生的'象外之象’”实际已涉及“意境”范畴,这一点也说明朱志荣的“美是意象”理论的不够圆融之处。朱志荣针对韩伟的观点提出了反驳,认为绝不能因为“意象”理论涉及“意境”范畴就不够圆融,其理由是:第一,意境所涉及的内容与意象差不多,都在强调其“情景交融”的特征。第二,意象与意境的关系,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意象侧重于感性形态,意境则更侧重于内在的精神层次,意境通过意象而呈现,在某种程度上说,意象也可以理解成意境。第三,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意象是单个的,而意境是由几个意象或整个意象群构成的,这与意象与意境是一体两面的观点并不矛盾。因为构成意境的,可以是单个意象及其背景,也可以是意象群组合而成一个整体的境象。第四,意象和意境所指称的特征是有所不同的。形神兼备,主要指意象的特征,虚实相生、动静相成则更侧重于描述意境的特征。最后,他还陈述了他为什么选择“意象”而不是“意境”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主要在于比起意境来,意象源远流长,形成了一个更为悠久的传统。而且它的意义相对更加稳定,可以捉摸,意境的含义则相对难以捉摸。再就是意象侧重于感性形态,相对具体,而意境侧重于内在特质,相对抽象。⑤
在中国古代美学中,意象与意境这两个范畴有着密切的关系,韩伟因为朱志荣的“意象”理论涉及“意境”范畴便批评它不够圆融,显然是过于草率。不过,韩伟认为虚实相生的“象外之象”是关于“意境”而非“意象”的一个本质规定,则比朱志荣将“意境”与“意象”看成一体两面的关系,认为意象和意境的本质都在于“情景交融”的看法,更能明确意象与意境之间的差异,说明意境与意象范畴的不同内涵。⑥我们并不否认朱志荣将“意象”与“意境”紧密联系起来看的观点的合理性,因为“意象”和“意境”范畴在中国古代的阐释视野中的确存在许多共同之处,如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天人合一”),有着共同的形象结构要素(情景交融)、共同的形象创构(重视语言表达的韵味与生命体验)。但并不意味着二者可以等同起来。这是因为,“意象”重在“意”与“象”、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把握,它“道”不离“器”,“象”不离“形”,是一个标识中国古代艺术形象本体结构和创造的范畴,而“意境”则超越有限的“象”,进入到一个无限丰富的联想与想象的艺术空间中,是一个标示中国古代审美意识和艺术境界“层深创构”(宗白华语)的美学范畴。所以“意境”与“意象”两个范畴虽有联系,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如叶朗所概括的那样,“意象”的基本规定就是情景交融,而“意境”除了有“意象”的一般规定性(情景交融)外,还有自己的特殊的规定性,那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到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11]。用宗白华的话说,“意境”是以虚实为底相,是“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12]。“意境”可以说是典型体现了中国古人的超越意识和形而上的审美追求,也可以说是“意象”中最富于形而上的人生体验和审美追求的一种类型。从这一意义上说,意象与意境的关系不能如朱志荣所理解的那样,是外在形态与内在境界和层次,意象也可以理解为意境的关系,应该将“意境”看成是产生于意象又超越意象的艺术创造。“意境”的妙谛不在象内,而在“象外”,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味”的审美虚空世界的创造,它是以主客一体、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形象来表现宇宙人生的丰富意蕴,从而激发出人们无限丰富的想象和情思,是艺术创造的高标准和高要求,并非只要是情景交融、能创造意象的艺术作品都能达到“意境”的审美层次。也不能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单体为象,合体为境”[13],即意象是单个的,而意境是由几个意象或整个意象群构成的,或者说“意境的范围比较大,通常指整首诗、几句诗或一句诗造成的境界,而意象只是构成意境的一些具体的细小的单位”[14],将意象仅仅作为意境创造的结构要素与手段看待,与物象、语象一类概念等同起来,而忽视意象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创造,是主客一体、物我交融的产物。
三、“美是意象”的理论缺陷
无论是朱志荣还是韩伟,其对“审美意象”问题的关注,都不在于将“意象”仅仅作为中西美学史上出现的重要范畴而肯定其价值,而是与中国当代美学关于“美”的讨论和美的本体理论建构密切相关。“意象”能否被看成美的本体,朱志荣与韩伟的文章观点截然相反。朱志荣对于“审美意象”的看法,不仅把“意象”作为中国古代艺术创造的本体范畴看待,而且也是作为美的本体范畴看待,认为“美是意象,是主客、物我交融的成果”,“我们通常所说的美,乃是审美意象,是审美体验的产物”[15]。而韩伟则否定“美是意象”说法,认为这一说法至少存在三个问题:混淆美与美的对象、美的观念之间的界限;对审美意象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模棱两可;欠缺理论的周延性和普遍性。
依笔者理解,朱志荣的“美是意象”说实际上包含这样几层意思:首先,认为“意象是审美活动创构起来的,是生命体验和创造的结果。其中既呈现了事物的本来面貌,也包含着人的主观感受,是情景融合的产物”⑦。意象创构不仅在个体审美活动中瞬间生成,而且也是社会的,是族类乃至人类在审美活动中历史地生成的。第二,从美的对象属性的意义上谈“意象”,认为审美意象是一种感性形象或者说是一种感性形态的存在,比如他说:“我们生活中被形容为'美’的感性形象,就是美学意义上的意象。”又说:“意象始终依托于感性形态。不管审美对象是否依托于物质形态,如自然界的梅花,油画等艺术品的画布,物象的感性形态才是审美活动的基础。”不过,审美意象虽然依托于感性对象的物态,其价值却是精神性的。第三,从“意象”的构成意义上谈“审美意象”,将审美意象分成“意”与“象”两个方面,其中的“象”,包括物象、事象及其背景作为实象,它“作为客观元素,诉诸感官,是意象创构的前提,是审美活动的基础”,也包括主体创造性的拟象,特别是在实象基础上想象力所创构的虚象,虚实结合,共同组成了与主体情意交融的象的整体。而“意”,主要指主体的情意,包括情、理和情理统一,包括情感和意蕴。意与象的交融,创构成审美的意象。“美是意象,是主客、物我交融的成果。”他还将“意象”与“心象”等同起来,认为“意象就是美及其呈现,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所形成的心象,是主体审美心理活动的成果”⑧。
从以上论述可见,朱志荣的“美是意象”说包含着一些合理因素,比如,它认为审美意象作为美的本体,是主体能动创造的结果,试图以生成的而不是预成的眼光看待审美意象的创构,认为意象创造不仅依托感性对象的物态,而且也包含情感价值评判等精神性因素,等等。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说法概念上存在着许多混淆,叙述方面也存在着叠床架屋、含混不清的毛病,在思维方式也没有摆脱传统的实体性和主客二分式思维方式的影响,所以远非是一个成熟,可以使人信服的理论。就“美是意象”的基本内涵和语义方面说,它起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没有明确“意象”与“审美意象”之间的区分。“意象”与“审美意象”,从概念使用的语义上来说,应该存在着“种”与“属”、类概念与亚概念的区分,也就是说“审美意象”应是“意象”的次属概念,二者之间应该有概念语义的区分,不能等同起来。而朱志荣的“美是意象”说显然将“意象”与“审美意象”作为同一层次的概念范畴使用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美是意象”的表述,就等于说是“美是审美意象”,完全是概念的同义反复,将“意象”作为美的本体的规定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并不能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美,或者说人们为什么将“意象”视为美。第二,“意象”到底是“物象”还是“心象”,是从对象属性还是从观念形态,是从感性物态还是从理性精神方面予以规定,朱志荣的“美是意象”说也较为模糊。从“我们生活中被形容为'美’的感性形象,就是美学意义上的意象”,“意象始终依托于感性形态”,“物象的感性形态才是审美活动的基础”,“意象主要指称美的外在感性形态”,“意象侧重于感性形态,意境则更侧重于内在的精神层次,意境通过意象而呈现”等观点表述来看,朱志荣的“美是意象”说,显然是将“意象”看成是一种审美对象,偏向于从对象属性,从物象的感性形态方面来规定“意象”的,可是从“审美意象作为美的本体,是主体能动创构的结果”,“是基于审美经验的价值判断”,“意象的创构体现了宇宙的创造精神”,“是生生不息生命精神的体现”,甚至将意象等同于心象,认为“意象就是美及其呈现,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所形成的心象”等等表述来看,朱志荣的“美是意象”说又将“意象”与“心象”等同起来,重在强调情感观念、主体心灵以及超越感性形态的理性精神对于“意象”创构的意义。第三,意象创构的主体与客体关系到底是一元的还是二元的,是主客一体还是主客二分,朱志荣的“美在意象”说也含混不清。论者提出“审美意象”说,其主观愿望显然是要破除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所以,他反复强调意象作为美的本体,是主客一体、物我交融的结果,并认为从中国传统美学中提炼出“审美意象”这一范畴本身就意味着对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超越,因为“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意象本身就不带有主客二元对立思维的烙印,审美意象本身就是对主客二元对立的超越”⑨。然而在事实的论证上,他又陷入了主客二分的理论窠臼,因为他所言“审美意象”,并非是主客一体的,而是主客分离的,是“意”+“象”的结果。“意”,包括情、理和情理统一等因素,属于主观层面的东西,而“象”则包括物象、事象及其背景作为实象(也包括主体创造性的拟象等因素),则主要属于客观层面。而审美意象正是在客观的物象、事象及其背景的基础上,主体通过主体的感知、动情的愉悦和想象力等因素而能动创构出来的,是主体的“意”与客体的“象”的相融相加的结果。这种思维和表述方式显然又带有明显的主客二分式的特征。
朱志荣“美是意象”说之所以存在上述的概念混淆,我以为主要还是在于他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虽然朱志荣也注意到,“审美意象作为美的本体,是生成的,不是预成的”,是在人的审美活动中历史地生成的,而他的实际论证,却始终不是从生成论的而是从预成论的眼光出发。“美是意象”,即美等同于意象,这一表述本身就是从一种预成(现成)论的思维眼光出发,将美看成是一种实体性的形象和对象的存在,与西方传统美学中的“美是理式”“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等美的本质问题解答的思路并无二致,都是在追问美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实存的具体对象是否存在,而不是回答人类为什么需要美,美如何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所以它与现代美学强调美的是生成的,不存在绝对美的本质,只存在美的现象和美的活动事实的美的本体论思路还存在很大距离。虽然,朱志荣也用了“审美活动”一类字眼,强调审美活动的过程就是意象创构的过程,审美活动(审美意象的创构)是基于审美经验的价值判断,似乎超越了实体性、预成论的思维方式,但是这只是一种理论的点缀,在实际论述中,朱志荣并没有将作为感性形态存在的美与作为情感价值判断的美统一起来,并没有从人与世界的关系,美对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方面看待审美意象的创构和生成,而是主要借用中国古代审美经验和艺术思维理论方面的成果(如《周易》《文心雕龙》等关于意象思维和审美经验的理论),同时也借鉴了一些现代美学的成果,如康德关于想象力在审美意象创造中居主导地位和朱光潜的“意象”乃是主体之意与客体之象融合的理论等来解释审美意象的创构与生成,对“意象”的美的本体价值认识基本还停留在传统的反映论(感应论)和表象心理学水平上,所以很难说是一种具有现代美学思维深度的理论。同样,朱志荣的“审美意象”理论之所以无法超越传统的主客二分式的思维方式,也在于它主要并不是从存在论,不是从人与世界、人与万物一体不分的关系看待“审美意象”的创构与生成,而主要是从人与世界所结成的情感认知的对象性关系来看待“审美意象”的生成,比如他说:“物象、事象及其背景作为客观元素,诉诸感官,是意象创构的前提,是审美活动的基础。它们通过'观’、'取’等方式被主体感受为眼中之象,即表象。这些表象中包含主体能动的拟象等,共同与主体的情意相融合而创构意象。”这里,重在强调如何将作为“象”的客观因素与作为“意”的主观因素叠加统一起来而创构审美意象,重在强调作为客观元素的物象、事象如何作为主体情感认知的对象而进入主体的视野中,并没有涉及主体的情感价值判断,也不是从人与世界、人与万物一体的关系看待审美意象的创构,其思维方式显然是主客二分而非主客一体的。
四、“美在意象”的阐释向度
韩伟在批评朱志荣的“美在意象”说的同时还对叶朗的“美是意象”说作了解读,认为叶朗提出“美在意象”说并非是在设法建构美的本体,而是明确将考察的对象限定在柏拉图所谓的“什么东西是美的”层面,因此他说“'美’在哪里呢?中国传统美学的回答是:'美’在意象”。并因此判定叶朗“美在意象”与朱志荣“美是意象”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前者属于性质描述或者说是将美视为意象的一种属性,而并非是对本质的抽象,而后者则将美固定化,侧重对美的定义。
韩伟说叶朗的“美在意象”说属于性质描述或者说将美视为意象的一种属性,而并非是对本质的抽象,有一定道理。虽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叶朗就将“意象”作为标识艺术本体的概念看待,90年代则明确提出“美在意象”说[16],但直到2009年出版的《美学原理》(又名《美在意象》)以“美在意象”为核心来建构其美学理论体系,都很少对“意象”和“美在意象”命题作出明确的理论定义。关于“意象”,叶朗最清晰的界定大概只有“中国传统美学给予'意象’的最一般的规定,是'情景交融’。中国传统美学认为,“'情’'景’的统一乃是审美意象的基本结构”[17]之类的表述。而关于“美在意象”这一命题,叶朗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而是将审美意象的创造与人的审美活动紧密联系起来,强调审美意象离不开审美活动,只能存在于审美活动中。并在此基础上,对“意象”的性质予以分析与描述,如“审美意象不是一种物理的存在,也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世界,而是一个完整的、充满意蕴、充满情趣的感性世界”,“审美意象不是一个既成的、实体化的存在,而是在审美活动的过程中生成的”,“审美意象显现一个真实的世界,即人与万物一体的世界”,“审美意象给人一种审美愉悦”等等。[18]不过,这种对审美意象性质的描述与分析并不能如韩伟所说,与美的本体建构无关,只是限定在“什么东西是美的层面”上。因为,叶朗提出“美在意象”说的目的还是在于美的本体建构。所以,叶朗尽管没有给“美”下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但从他的基本论述来看,显然是要把美的本体归到意象上来。比如他说:“在中国传统美学看来,意象是美的本体,意象也是艺术的本体”[19];评价朱光潜的美不是“物”而是“物的形象”(物乙)说时,亦明确将它归结为“意象”,认为“朱光潜在这里明确说,意象就是美的本体”[20]。在他的著作中,还多次使用了“审美对象(美)是'意象’”之类的表述,并常常在“美”这个词后面用括号注上“意象”或“意象世界”,将“美”与“意象”(意象世界)等同起来。
不可否认,叶朗使用“意象是美的本体,意象也是艺术的本体”,“审美对象(美)是'意象’”之类的表述,在逻辑概念上存在着不严谨和语义不清之处。他似乎与朱志荣一样,也将意象看成一个既定的术语,并与美等同起来,认为意象就是美本身,就是艺术本身。这样的表述,显然也还带有实体性和现成论的思维特征。不过这并不能否定叶朗“美在意象”说的理论价值以及它与朱志荣“美是意象”说的本质差异。这种价值与差异就在于,“美在意象”说对美的本质理解,已从传统的认识论转向了审美生存论,从主客二分转向了天人合一,从现成论转向了生成论。叶朗“美在意象”这一命题关键性的理解,应该是落实在“在”(而非“是”)上,“美在意象”命题意在说明的是,美以意象形态的方式存在,或者说美是通过意象表现出来的,是“在”而不是“是”。那么,意象与美之间就不能简单地画等号,意象就不能等同于美本身,而只能说,意象作为美的现象显现着美的本体,意象是人的审美活动与审美体验的产物。作为意象形态存在的美,绝不能看成是对象化的实体形象存在,也不能看成是主观精神的产物,因为它既明确否定了实体化、外在于人的“美”,也否定了实体化、纯粹主观的“美”,它实际上是对传统的主客二分式的美的本质化思路的突破,美作为本体的存在,已不再具有实体性、对象化的意义,它只意在说明美的本体规定与人的审美活动不可分,审美意象只能存在于审美活动中。所以,叶朗“美在意象”命题的提出,并不像朱志荣那样,重在将“意象”作为一个实体范畴,将“意象”分解为物象、事象、拟象等多种元素,对“意象”(美)的本体作出抽象的解读和规定,也不是像朱志荣那样,将“意象”等同于美的感性形态(感性形象),偏于从感性形态的层面而不是从价值评判的层面来看待审美意象的创构与生成,而是突出审美意象的创造对于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所以他将“美”(意象世界)描述为“一个完整的、充满意蕴、充满情趣的感性世界”,并认为“意象世界是人的创造,而正是这个意象世界照亮了生活世界的本来面貌”[21],“世界万物由于人的意识而被照亮,被唤醒,从而构成一个充满意蕴的意象世界。意象世界是不能脱离审美活动而存在。美只能存在于美感活动中”[22]。这正是叶朗“美在意象”说的理论精义所在,它从美与美感的同一性,从美与人生关系以及价值评判的层面上彰显了“意象”作为美的本体存在的意义,而朱志荣的“美是意象”说在这方面则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与不足。
注释:
①如《谈美》中所说的“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论文学》所说的“凡是文艺都是根据现实世界而铸成另一超现实的意象世界”,《诗论》所说“每个诗的境界都必有'情趣’和'意象’两个要素、'情趣’简称'情’,'意象’简称'景’”,等等。
②朱志荣:《论审美意象的创构过程》,《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③朱志荣的观点主要见于《论审美意象的创构》,载《学术月刊》2014年第5期,韩伟的观点主要见于《美是意象吗》一文,载《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笔者本文要辨析的观点主要是针对这两篇文章,凡引用于这两篇文章中的文字与观点不再标明出处。
④参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202页。
⑤朱志荣的观点,除了《论审美意象的创构》一文有系统表述外,还见于他的《再论审美意象的创构》一文。这里所引用的观点,是根据这两篇文章综合而成的。
⑥朱志荣的观点实际上存在许多含混之处,一方面他认为意象与意境都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另一方面又认为,意境是从境界角度指称意象,更侧重于强调内在气韵、神韵等。所以形神兼备主要指意象的特征,虚实相生、动静相成则更侧重于描述意境的特征。一方面认为意象主要指称美的外在感性形态,另一方面又将意象作为美的本体,是主体能动创造的结果。
⑦朱志荣:《再论审美意象的创构——答韩伟先生》,《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
⑧关于朱志荣“美是意象”说的观点,笔者主要综合朱志荣的《论审美意象的创构》和《再论审美意象的创构》两篇文章观点而成。
⑨朱志荣:《再论审美意象的创构——答韩伟先生》,《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
原文参考文献:
[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02页。
[2][3][5]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201、201、202~203页。
[4]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42页。
[6]周发祥:《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20~121页。
[7]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60页。
[8]苏珊·朗格:《情感的形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58页。
[9]萨特:《想象心理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123页。
[10]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页。
[11][16]叶朗:《胸中之竹——走向现代中国之美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7、267页。
[12]《宗白华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12页。
[13]古风:《意境探微》,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96页。
[14]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4页。
[15]朱志荣:《中国审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3页。

文心 诗情 博物 乐境
青少儿人文美育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