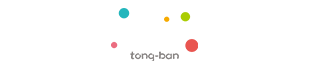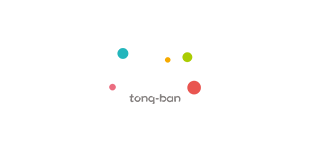在宗白华的美学思想中,意境理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早在40年代初,宗白华就满怀豪情地说:“现代的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新的局面必将展开……就中国艺术方面——这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最有世界贡献的一方面——研寻其意境的结构,以窥探中国心灵的幽情壮采,是民族文化的自省工作。”而他毕生的美学研究,均实践着这一宏愿。宗白华的意境理论博大精深,全面揭示其理论精髓非本文所能。下面仅结合当前意境理论研究的实际,就自己感兴趣的几个问题谈谈学习宗白华意境论的体会。

一
任何美学理论都有自己的哲学根基。意境,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更不能例外。宗白华的意境理论,尤其重视揭示这一点,他说:“中国画所表现的境界特征,可以说是根基于中国民族的基本哲学,即《易经》的宇宙观,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禀天地之气以生……这生生不已的阴阳二气织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中国画的主题'气韵生动’,就是'生命的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又说:“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一切艺术境界都根基于此。”
本来,意境根源于民族的基本哲学观念,根源于中国古人根本的宇宙生命意识,也是中国古人所深刻感悟的。中国古人言意境,常有“宇宙在手”、天地境界之说,便是如此。许多美学家,如司空图、王夫之等言意境,所重的也是意境创造的那种宇宙生命意蕴和气象。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古典意境说这一精髓,在近现代许多研究意境理论的人那里被忽视。许多人热衷于以西方哲学美学理论为据来阐释意境,却忽视意境理论自身的哲学的根源和传统。比如,解放前,朱光潜先生以克罗齐的直觉说为据,把“意境”说成是“用'直觉’见出来的”,是直觉到的情趣与意象的契合统一;解放后,则长期流行这样的看法,即视意境为典型的一种,把意境看作是主客观高度统一的典型形象,等等,就是如此。所以,宗白华这一揭示是有特殊意义的。事实上,意境是决不能用典型说一类说法来加以阐释的,这是因为二者的哲学根基根本不同。典型论实际上是以西方古典哲学和摹仿论为基础的,而意境则是中国古人那广大和谐的宇宙生命意识的体现。今道友信把东方美学称为超越的美学,认为它“向人类启示了宇宙的神韵”,“启示了超越者的美”,而这种启示和超越性突出表现在意境美的创造和追求上。拿“意境”和“典型”相比,在表现宇宙人生意蕴和精神超越性方面,“意境”无疑处在更高层面,无疑要深刻得多,忽视了这一点,任何对意境理论的描述和揭示,都是没有意义的。
意境根源于中国古人的根本哲学观念,由这一观点出发,意境显然也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意与境、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持“意境”为“典型”论的人把意境分为意与境,即生活形象的客观反映和艺术家情感理想的主观创造两个方面,认为“意”、“境”就是这两方面的高度统一。宗白华言意境,与上述看法显然不同,他极少用主客观统一之类的字眼,而是强调它是艺术家主体心灵和宇宙诗心的体现,是“艺术家凭借他深静的心襟,发现宇宙间深沉的境地”,是艺术家主体生命与客体对象生命的交融互渗。他说:“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宇宙诗心, 主体生命与客观景象交融互渗的说法,不能等同于意与境、主观与客观统一的说法,它源于中国古代那天人合一的宇宙生命哲学意识,所重的是人与宇宙生命的和合沟通,人的精神价值在宇宙天地境界中的实现,而非西方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下那种心反映物,意表现境的主客观统一。宗白华言意境,常常又把它称为心境、心中的灵境等,这也正是古代意境理论的题中之义。中国古代自《乐记》提出“乐者……其本在人心感于物”这一命题以来,就特别重视心与物的交融和“心”在这种交融中的作用,认为“本于心”的创作远高于“本于物”的创作。“意境”正是这种文化观念和艺术精神的产物。它作为一个审美范畴,是重在“心”、重在“意”,深浸着主体心灵意味的。王昌龄曰:“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苏轼曰:“意与境会”;方回曰:“心即境”;方士庶曰:“因心造境”;林纾曰:“境者,意中之境”;梁启超曰:“境者,心造也”;等等,都说明了这点。宗白华的意境论是深刻地感悟着传统哲学美学这一精神内涵的。
宗白华对意境理论哲学根基的揭示,实际上也否定了那种认为意境源于佛家禅宗哲学的看法。宗白华并不否认佛学禅宗思想对意境理论的影响,他把禅境看作中国艺术理想境界的实现,但是亦强调“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认为禅并没有割断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联系。宗白华对意境理论哲学根基的揭示,是在儒、道、释三家哲学圆融通合的大哲学背景下展开的,他把意境看作是人类生命情调的表现,是生生不息,变易无穷,对宇宙生命有深刻感悟的审美范畴,所以,他又尤其重视肇始于道家的“道”为宇宙生命本源,“道”的体验构成意境审美的生命和实质的思想。他说:“中国哲学就是生命体悟'道’的节奏,'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的形象和生命,'道’给了'艺’以深度和灵魂。”又说:“中国人对'道’的体验,是'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唯道集虚,体用不二,这构成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和艺术意境的实相。”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就是'道’,中国哲学美学的基本精神就是体道悟道,这是许多人都意识到的,宗白华把它特别揭示出来,显然有助于我们把握传统意境理论的真谛。他所谓体道悟道,也就是强调“意境”美创造离不开宇宙人生真相的揭示,强调意境的根源仍在于活泼泼、气象万千的宇宙人生世界,这与那些鼓吹清虚玄远、不食人间烟火的佛家意境论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他的意境理论,也正是从“道”的生命体悟出发,到流动、虚灵的节奏化、音乐化的艺术空间展现,再到富于诗意的艺术人生的体验和创造,构成一完整的艺术理论系统,从而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二
宗白华言意境,又尤重虚实的审美意义。他说:“虚实为意境的底相”,“化实景为虚境,创形象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可以认为,宗白华把“虚”、“实”看成意境构成的两元,认为中国艺术意境就是“虚”“实”的统一,是“以虚带实,以实带虚;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虚实结合。
宗白华重“虚”“实”在意境审美中的意义,对我们深入理解意境本质特征,亦十分重要。当今理论界言意境,有一常见看法,那就是把意境本质归结为“情景交融”,认为情景相生、情景交融就是有意境。应该承认,这一说法注意到意境形象塑造的某些特征,有一定合理性。意境的形象创造,也确包含着情景交融的因素。对于这一点,宗白华先生也不否认。他说:“'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品。”但是, 仅仅停留在情景交融上,对意境本质的认识还是浅层次的。以情景交融言意境,远没有充分揭示出“意境”范畴内涵和层次结构的丰富性,揭示出意境与中国古代哲学、美学意识极其深刻内在的联系,而是把它与中国古代艺术形象的一般范畴,即审美意象范畴等同起来,从而大大地降低了意境理论的思维层次。事实上,中国古人有关情景交融的看法,虽有“情景者境界也”(布颜图语)的说法,与意境相关,但多不是从“意境”本体生成角度,并没有明确将情景交融置于意境的义项之下。比如,范xī@①文曰:“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情景相融而莫分也”;谢榛曰:“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夫情景相融而成诗,此作家之常也”(《四溟诗话》);王国维曰:“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文学小言》)等等,都是就中国古代诗歌艺术形象,即审美意象创造的一般规律而言,而非特指意境。
以虚实言意境则不然,它比情景说大大进了一个层次,不再停留在艺术形象(审美意象)的一般规律上,而是着力揭示意境审美的特殊本质和规律。宗白华说,“虚和实的问题,这是一个哲学宇宙观的问题”,虚、实代表着中国古人根本的宇宙观和世界观,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国艺术审美精神。以虚实言意境,当然不是不讲意境的情景关系,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情与景的因素,若离开了中国美学虚实结合审美理想和精神观照,不在虚实结合中相互转化和开拓,展示宇宙无限的生命图景,就还是浅层次的,谈不上什么意境创造。所以,宗白华言意境,从不停留在“情景交融”的层面上,而是以虚实为本,提出有关艺术意境创造的一系列原则和思想:
第一,“化景物为情思”的原则。
宗白华认为,“化景物为情思”,“这是对艺术中虚实结合的正确定义”,“实化成虚,虚实结合,情感和景物结合,这就提高了艺术的境界。”“化景物为情思”,实际上讲的也是意境创造中的主客体辩证关系,它要求艺术家不机械地复制现实,而是“化实为虚”,深刻表现艺术家对宇宙人生的心灵感受和体验,从而创造韵味无穷的艺术境界来。
第二,“境界层深的创构”说。
宗白华认为:“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从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层次。”宗白华这一看法本于古人, 王昌龄有物境、情境、灵境三境之说,蔡小石有词的始读、再读、卒读三境层说,江顺贻有“始境”、“又境”、“终境”三境说,均可以与宗白华意境三层次说相对应。不过,宗先生明确把它纳入虚实审美法则之中,强调意境层层深入以致无穷的审美意味,并特别突出“灵境”,即主体人格和心灵在意境创造中的作用,则大大发展了古人的意境层深结构说,对我们认识意境的本质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空白”说。
宗白华说:“中国画最重空白处,空白处并非真实,乃灵气往来生命之处。”“空白”并不是纯粹的空无, 它是艺术境界的虚实要素,“代表着中国人的宇宙意识。”“空白”美的产生,亦全赖艺术创作中虚实审美法则的运用。宗白华说:“'唯道集虚’,中国诗词文章都重这空中点染,抟虚成实的表现方法,使诗境、词境里面有空间、有荡漾,和中国画具有同样的意境结构”。宗白华提出“ 空白”说,还意在说明中国古人对宇宙人生有一种独特体验, 所突出的正是中国古人所特有的宇宙时空意识和崇尚空灵的审美价值取向,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意境审美的精神本质所在。
第四,飞动之美。
由意境的虚实结合和空白美的追求表现,“意境”创造又自然追求飞动之美。飞动之美,亦说明意境作为一个审美空间,不是一片死寂的空间,而是充满宇宙生命活力和节奏的空间,努力写出意境的飞动之美,显然也是创造意境的重要法门。宗白华亦以“舞”为典型代表来说明这点。他说:“天地是舞,是诗,是音乐,中国绘画境界的特点建筑在这上面。”又说:“中国的书法、画法都趋向飞舞,庄严的建筑也有飞檐表现着舞姿”, 他还以杜甫诗句“精微穿溟滓,飞动摧霹雳”为例,说明诗歌也以飞舞的意象为最高境界。
总之,宗白华以虚实为本言意境,大大丰富了人们对意境本质特征的认识,使人们不再停留在“情景交融”的单一视角上,而向着民族的、诗意的、富于人生哲理意蕴的立体纵深方面发展。
三
宗白华的意境论,还有一显著特征,那就是他几乎从不在狭隘的诗学意义上使用“意境”这一概念范畴,把“意境”局于纯诗艺的创造和鉴赏的领域,而是涵盖着一切美的艺术和人生,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存在,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思考。他说:“什么是意境?人与世界接触,因关系的层次不同,可有五种境界……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这里,宗先生明确把艺术境界看作是人对世界的关系层次的反映,看作是人类最高心灵的体现。他认为:“艺术不只是具有美的价值,且富有对人生的意义、深入心灵的影响。”伟大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它“启于宇宙人生之最深的意义与境界。”由这一深沉的艺术人生信念和关怀出发,宗白华又尤重主体心灵和人格修养对意境创造的意义。他说:“意境是艺术家的独创,是从他最深刻'心源’和'造化’接触时突然的领悟和震动中诞生的”,艺术境界的实现,“端赖艺术家平素的精神涵养、天机的培养。”同时,他还对艺术家的人格涵养和心灵培养提出了两个具体要求:一是要“空灵”,所谓空灵就是超越现实功利考虑,以“不沾带于物的自由精神”静观万物,使万物都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二是要“充实”, 宗白华说:“ 艺术境界中的空灵并不是真正的空,乃是由此获得'充实’。 ”“充实”来自于“生活经验的充实和情感的丰富”,它是宇宙人生“壮阔而深邃的生活的具体表现”。“空灵”与“充实”的辩证统一,便是艺术家心灵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宗白华还指出,在中国古代艺术中,“意境高超莹洁而有壮阔幽深的宇宙意识生命情调的作品”是不可多见的,只有少数艺术家, 如杜甫、李白、王维等才能达到这一点。他们的作品意境高、深、大,“都植根一个活跃的、至动而有韵律的心灵”,没有这心灵和超迈高洁的胸襟, 就谈不上真正的意境创造。
宗白华的上述看法,可以说是深刻揭示了意境与人生、与人的胸襟、人格力量的关系,对我们把握意境的精神本质很有启发意义。时下不少人言意境,喜欢从纯文学、纯艺术的角度,把意境只作为一个纯艺术理论批评的概念范畴来理解,认为意境只是古典的、抒情的、表现型艺术的范畴,甚至认为它只出现在中国古代审美的某个特定时期(唐中叶至明),所探讨的问题也多限于意境的艺术表现特征,如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真切自然、有言外之意、韵外之旨等等。我们当然不能否认这种理论研究的价值,但仅限于此一隅,则大大缩小了意境的理论意义。其实,意境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它并不只是纯艺术批评理论方面的范畴,而且也是作为体现传统文化精神和中国古人心灵生存空间的审美哲学方面的范畴。它所关注的问题,也非只是艺术表现特征的问题,而首先是人生、人的生命价值、人格精神建构的问题。这一点,中国古人亦常常感悟到了。中国古人言意境,有所谓“体道”、“适性”、“取境”、“观物”,“观我”、“忧世”、“忧生”、“真境”、“宇宙气象”、“天地境界”之说等等,便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司空图为古代意境说的典型代表,其意境理论精神显然远超出纯诗艺之一隅。刘熙载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足为一己陶胸次也”,就是说司空图意境论重在止泊精神,安抚身心,具有陶养人之性情与胸襟之功用。《诗品·实境》曰:“取语甚直,计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见道心……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泠然希音。”这里所言“道心”,“情性”,都是强调主体胸襟、人格精神对意境创造的作用,他所谓二十四种诗歌风格境界,也完全可以看成是二十四种人格境界。况周颐言“词境”曰:“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而能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也。”这“吾听风雨、吾览江山”的“词心”说,乃是讲人的生命体验和感悟,它显然是艺术意境得以创造的基本前提。王国维言意境,主张“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方成高格”,“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所设,世无诗人,即无此境界”等等,更是从人生、人格精神和心灵方面立论,其意义决非只限于纯艺术表现一隅。可以说,宗白华的意境论正是承继了古典意境论这一精神并予以发场光大,它实际上也构成了意境论极具生命力、极具现代意义的一个方面,值得我们格外珍视。
四
宗白华说:“美学的内容,不一定在于哲学的分析,逻辑的考察,也可以在于人物的趣谈,风度的的行动,可以在于艺术家的实践所启示的美的体会或体验。”不重哲学的分析、逻辑的考察,而重趣谈、风度、艺术和审美的体验,这是宗白华美学的显著特色,亦典型地体现在他的意境理论和审美实践中。他的意境论,不是从逻辑定义和概念辨析出发,而是从美的体会或体验出发,不是纠缠于有关意境的本质、对象、特征的空泛讨论,而是凭借自己深沉的心襟去充分领略、感受艺术人生中的意境美。他的许多论述,比如,说:“中国人与西洋人同爱无尽空间,但此中有很大的精神意境上的不同”;中国人对空间的态度不像西方人那样“失落于无穷,驰于无极”,而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中西画法所表现的'境界’根本不同,一为写实的,一为虚灵的,一为物我对立的,一为物我浑融的”等等,都似是漫不经意的心灵偶得和诗意点染,但又深得中西意境审美之神髓。他尤其喜欢结合中国艺术来谈意境,对中国各类艺术在表现方法和精神境界方面的特征都有很深的感悟和体验。这些,又都成为当代意境理论最深沉精辟的探索和最精美的华章。宗白华意境论的这一特色和方法,亦给我以深刻的启示。在当前的意境理论研究中,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执于意境概念定义之争,企图以西方的那种科学理性和逻辑分析方法给“意境”以确定的、明晰的定位,而是不是像宗白华那样凭借丰富的艺术心灵,投身民族的艺术实践,去充分领略感受意境的美。一位意境理论的研究者曾这样感叹:“意境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它的概念还在发展和丰富着:或看作思想境界,或看作思想艺术达到的程度,或看作艺术特征,或看作诗中意象,或看作整体形象,或看作人物塑造的表现手段,或看作作家的整体构思,或看作立体的审美空间景象,或看作情景交融,或看作贯注形象的意脉……”有关“意境”的定义如此之多,可见意境定义之争已达到相当俗滥地步,意境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范畴,这不能不说是意境理论研究的悲哀和方法上的重大失误。事实上,意境作为一个美学范畴被命名,是以民族的诗意审美和艺术实践为基础的,它只能在民族的诗意的体验中呈观,而不能以西方美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予以条分缕析的逻辑论证和定位。在宗白华之前,王国维以“意境”范畴为中心,建构自己的艺术理论系统,其重心亦在令人震颤的艺术人生体验,我们尽可以批评王氏意境范畴概念不明晰、不严格,易引起误解和混乱,但我们却无法否认他以“意境”为中心,对传统艺术精神的深刻感悟和发现。宗白华意境论也是如此,它作为一个理论范畴,也有非常宽泛、不严格的地方。但由这一范畴为核心所建构起来的,不同于传统认识论美学的重体验、重感兴的理论风貌,却给人以深刻启示,即美学理论也可以是诗性感悟的、非系统非规范性的,我们也应从这方面去发展美学,而不是只停留在科学的、规范系统的美学理论形态上。

文心 诗情 博物 乐境
青少儿人文美育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