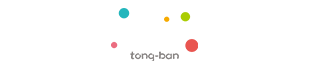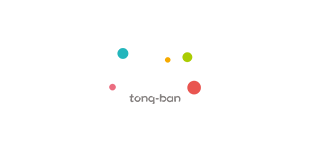一、 什么是意境?
意境恐怕是中国美学当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范畴了,对于意境的研究古已有之。何谓意境?这恐怕是研究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的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意境的阐释甚至可以成就一片学术领域。宗白华先生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恐怕是这一领域公认的内涵最丰富、见解最精辟的了。
意境是什么?意境首先是一种境界,或者直接称为“境”。[1]宗先生此文认为境界是人对于其所接触的世界形成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概括出五种境界:功利境界、伦理境界、政治境界、学术境界与宗教境界。很奇怪,该文所探讨的意境却不在这五种境界当中,意境所对应的境界是艺术境界,宗先生认为艺术境界介于学术境界与宗教境界之间:“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但介乎后二者的中间,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2]这或许是为了强调出“艺术境界”从而引出该文所探讨的核心概念——意境,是一种修饰的方法,还是别有深意?思之不得其解。然而,注意到此处对艺术境界的阐释,是“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是一种对象化或称客体化的东西,是一种心灵的反映,它又化实为虚。这让我想起在关于中国艺术的探讨的文章中常常引用的郑板桥画竹的例子:“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对于“眼中之竹”,是作为对象来把玩的,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则是化实为虚,然而,还要把这种“虚境”还原为对象,客体,即所谓的使心灵“具体化、肉身化”。因此,“胸中之竹”之后尚有下文:“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3]到此,“艺术境界”全出。然而,这种“境界”是一种对象化的主观情思,它来源于客体——“眼中之竹”,而又还原于客体——“手中之竹”。在两者之间——“胸中之竹”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说,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艺术中两种客体间得以转化?
答案是心灵:“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谓美的。”[4]王国维于《人间词话》中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由此看来,“意境”一词的使用,是要比“境界”更完备的,除了“境”,它还强调“意”,即“游心之所在”。“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5]
意境由客观的境界和心灵的映射构成,其主要的特征便是情景交融。这一观点几乎成为中国美学界的共识,其类似的表达也见于与宗先生齐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文艺作品都必具有完整性。它是旧经验的新综合,它的精彩就全在这综合上面见出。在未综合之前,意象是散漫零乱的;在既综合之后,意象是谐和整一的。这种综合的原动力就是情感。”[6]朱光潜显然将意象看作是客观的,也就是所谓的“旧经验”,而其“新综合”的动力则是主观的情感。在五十年代大陆美学的大讨论中朱先生独树一帜地提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或许就是出于这种观点吧。关于这种统一,即意象与情趣的契合,朱先生是用“移情作用”和“内模仿作用”来说明的。借用西方美学理论来说明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并无不可,但无论是“移情”还是“内模仿”难得其真髓,总让人有一点言之未尽的感觉。在“意境”中,主客观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既然“统一”难得真味,李泽厚则用“扬弃”一词来说明这种统一。[7]却不及宗先生那么诗意与自然的阐释:“情和景交融互渗,因而发掘出最深的情,一层比一层更深的情,同时也渗入了最深的景,一层比一层更晶莹的景。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为景,因而涌现了一个独特的宇宙,崭新的意象,为人类增加了丰富的想象,替世界开辟了新景。”[8]这种“独特的宇宙”与“新景”即是意境。它不是情与景的简单统一,而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交融。它是意象,却是“崭新的意象”。正如该文中也引用过的那首著名的《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借着最后一句的点睛之笔,全篇既非仅仅是景,也非仅仅是情,而是既是景也是情了,由此可见其意境——“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为景”。
或许,“意境”这个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与中国哲学中的“道”一般,都是难以用语言准确表达的,“道可道,非常道”,是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难怪有人说试图解释“意境”容易走向歧途。
二、 中国艺术意境的诞生
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宗先生在探讨了“意境”之后,指出意境创现的基本条件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在这个基础上讨论中国艺术意境的创现(诞生),脉络很清晰。基本上,中国艺术意境的诞生可以分为三步:[9]
第一步,直观感相的模写——造化——写实;
第二步,活跃生命的传达——心源——传神;
第三步,最高灵境的启示——禅境——妙悟。
以下分而述之。
(1) 外师造化
“造化钟神秀”(杜甫诗),审美感兴总是从外物开始的。意境是情景的交融,意境的创现也就离不开情和景两个方面。所谓外师造化,就是在艺术创造与审美感兴中构建的客体对象。无论是艺术创造还是审美感兴的最后目的就是达到一个自由的自我世界,这世界不是凭空出现于意识中,而是经由一个感兴的过程达到的,所感之物就是感兴的起点。所感之物可能是一片自然风景,也可能是一件艺术品。因此,可以说,外师造化是艺术意境诞生的源起,是一个起点。
对于一个艺术创作者而言,这造化总是自然之物。宗先生在讲造化时,讲的便是山水。“山水之为物,禀造化之秀。”(元人汤采真语)
可感之物所在多矣,宗先生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为何单讲山水?按照该文的说法,这是因为:“艺术意境的创构是使客观景象作我主观情思的象征。我人心中情思起伏,波澜变化,仪态万千,不是一个固定的物象轮廓能够如量表出,只有大自然全幅生动的山川草木,云烟明晦,才足以表象我们的胸襟里蓬勃无尽的灵感气韵。”[10]如何理解?这话似乎是说,造化并不仅仅是客观的东西,它的呈现带有人的参与,是主观情思的“如量表出”。若是没有人这一审美主体的参与,也就无所谓造化。
这让我想起陆九渊讲的“我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我心”,我所知道的宇宙只是我心而已,这造化也不过就是我心的映射。“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11]王阳明讲的是心外无物,而我则引用此话来解释造化,造化便是这么一个东西,它看上去是客观的,实则是我心中的客体,而艺术家对于意境的营造则是要让这原本“归于寂”的烂漫春花“一时明白起来”。审美主体也是通过感兴达到这“一时明白起来”的意境。
我觉得,宇宙不全是我心。康德把物自体和表象区分开来,认为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只是物自体向我们显现的表象,而那些没有显现的是我们所不可知的部分。这种显现是向着人的显现,是一种双向的作用,人必然地戴着“感性直观的先验形式”这么一副眼睛去看世界。然而,其实造化——可感之物又比表象的外延要小。世界在向我们显现,而我们在理论上虽然可以认识所有的表象,但我们只注意其中的一部分,而造化更是其中可兴的一部分。[12]
格式塔心理学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启示。“格式塔”来自德文词Gestalt,是指经过知觉组织过的经验中的整体。这一内涵给我的最大的启示就是在感知事物时,知觉的组织作用的参与。人对外部世界的对象并非消极地接受,而是主动地加以选择。这种选择性决定于观赏者的个性、需要、生活经验、思维定势和观察角度。[13]例如面对一片树林,木材商人、植物学家和艺术家的态度就肯定会有所不同。[14]
回到前面提出过的问题:为何宗先生讲到造化时单讲山水?综上可知,造化便是审美主体对客体的主动选择。它虽然是客体,但是参进了主体意识,是被选择了的客体。而之所以选择山水,恐怕需要在“全幅”和“生动”两个词上揣摩,山水是主体的选择,这选择本身便是主体丰富内涵的流出,是全部情感和“灵感气韵”源源不断地流出,只有具备“全幅”和“生动”的山水才能表现。当一个人具备足够丰富的内在情感时,当他与世界相遇——也即是当情感与意象契合之时——就自然地要惊异,要感兴,要升华,要欢喜赞叹,“赞天地之化育”。山水是再恰当不过的造化了。当然,对一花一叶也能有其感,有其兴,有其造化,然而,这不过是全部丰富内在情感的一部分,或者,在有些人看来,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既然造化是主体对于其建构的审美客体而言的,那么,对主体就必然有内在的要求,这便是心源了。
(2) 中得心源
“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闪烁的星空与我心中的道德律。”(康德)在与那灿烂永恒的星空接触一瞬间,心中的道德律就流窜出来,敬畏的不仅是星空,也是心中的道德律。与其说是伦理境界,不如说是一种艺术境界,一种意境。这“心中的道德律”便是中得心源。宗先生或可认同。在该文中就专门讲到艺术家的人格涵养。以前就常听到类似“看字如看人”,“作文如做人”之类的教条,想来是有一些道理的。要与世界相遇,自己心中怎能没有世界?要与宇宙交融,心中不能没有宇宙。一个内心龌龊的人又怎么能达到艺术的意境?
“这种微妙境界的实现,端赖艺术家平素的精神涵养,天机的培植,在活泼泼的心灵飞跃而又凝神寂照的体验中突然地成就。”[15]在达到意境的路上,在心源的这一部分,需要的条件至少有三个:精神涵养、天机培植、心灵的飞跃与寂照合一。
为何需要精神涵养?如前所说,我心中的灵感气韵,是需要“全幅”与“生动”的山水才能“如量表出”的,这种量的表出,看上去像是一种崇高的审美形态,其实不然。康德认为崇高表现为数量的崇高与力的崇高,其无限巨大与无穷威力超过了主体对表象直观的感兴综合能力所能把握的限度,是对象对主体的否定。主体与对象是处在一种尖锐冲突的状态。这显然是与中国艺术有所不同的。“全幅”与“生动”的山水展示的并不是对渺小的人的否定,而是直接与创作者心中的天地相合的。这里看到的不是对立,而是和谐,是主观情趣与对象意象的契合。若是心中没有一片洁净的天地,其创作的山水有怎能与艺术家的内心相一致呢?高尚的人格涵养才能造就高超的艺术意境。
王夫之说:“有物于此,过乎吾前,而或见焉,或不见焉。其不见者非物不来也,己不往也。”(《尚书引义·大禹谟二》)其见与不见之间,天机立判。关于天机的培植,或许是一个审美教育的问题。一个缺少天机的人,对于世界是视而不见的,只有通过对天机的培植,才能使一个人具有艺术的敏感,能够在与世界相遇的那一刹那产生审美感兴而通达意境。“艺术境界的显现,绝不是纯客观地机械地描摹自然,而以'心匠自得为高’。”[16]心匠者,天机也。
最后,“在活泼泼的心灵飞跃而又凝神寂照的体验中突然地成就”似乎不太好理解。宗先生说静穆的观照与飞跃的生命是艺术的两元。[17]经过精神涵养和天机培养,要“中得心源”尚需最后一步,即将精神涵养和天机相统一,从精神涵养中可以得到活泼的心灵,一个人性的、艺术的、敏感的,时刻感受着生命律动的心灵。然而,作为通向中国艺术意境的心源,只有活泼的心灵是不够的,这心源不是意识流的。它还需要“凝神寂照”,即对审美客体的观照,这种观照是出自心灵的敏感的,是加以艺术选择的观照。将活跃的心灵贯通于凝神寂照。朱光潜先生说得好:“情趣是可比喻而不可直接描绘的实感,如果不附丽到具体的意象上去,就根本没有可见的形象。”[18]一个对美,对艺术敏感的自我观照着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心是活跃的,律动着的,胸中包藏万象,感受着这世界,这寂静无言的宇宙,在人与自然的沟通中上升到一种灵境。到此时便是超以象外而得其环中了。
(3)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19]此言表明意境,然而,总觉得有所不足,意与境相“浑”固然有理,然“浑”却不一定能够上升到灵境,还需要某种升华的作用。
宗先生的一段话说得精彩:“所以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不但是盛唐人的诗境,也是宋元人的画境。”[20]既要一往情深,又需无迹可寻,似有似无,欲说还休,言不尽意,意在言外。所谓空色之辩,也就到了一种禅境,直接是灵魂最深处的灵境启示,是个人的体验与宇宙的鸿蒙之理合而为一。万物与我合而为一。是“道可道,非常道”。(《老子》)除非以艺术的方式,难以表达出这种境界。中国的艺术是体验的艺术,中国的美学是意境的美学。这或许出于中国人对语言的不信任,或许如我等才浅艺微,实难理解大家之言。维特根斯坦教导我们对于不可知之事,要保持沉默。宗先生固然有所启示,无论我是真的读明白了,还是自以为明白了,似乎都不便于在此言说,我也无此能力言说,引陶潜《饮酒》一首述之:
陶潜《饮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我恐怕也是“欲辨已忘言”了。突然注意到,外师造化,有艺术与哲学的关系;中得心源,有艺术与伦理的关系;而灵境的启示则似乎有一点宗教的气韵在里面。或许,在中国艺术意境当中,艺术、哲学、伦理、宗教四者是同一的。
从“外师造化”到“中得心源”再到“最高灵境的启示”,也即是“写实”——“传神”——“妙悟”,是中国艺术意境创现的步骤,但这三步的划分是逻辑上的顺序。实际上三步是一气呵成,无先后之分的。写实直接就是传神,而传神与写实直接抵达妙悟的意境。“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与“最高灵境的启示”原本就是同一个过程。
三、 中国艺术意境的形而上原理——道
“道”是中国艺术意境诞生的本体论依据,或称形而上学依据,也是中国艺术意境理论与中国哲学的最重要范畴之一。中国哲学中对“道”的解释大致有三个源头。
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道”的概念相当于礼仪规范,人生与治国的准则,“道”与“命”是分不开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中庸》第一章)且直接受“命”的影响:“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
第二种来自对《易》的解释,“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系辞上》),“道”作为阴阳的变化规则,是宇宙间相互对立并且相互依存的矛盾统一的普遍法则,是宇宙大化的规律。
还有一种主要的解释来自老子。在老子那里,“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万物的创造者,是一种类似于最高实体的东西,但是却是不可言说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二十五章)具体事物皆是为他物所限,须依赖他物而存在,而道“先天地生”,不依赖他物,不为他物所限,作为万物之本,是无形无象,不生不灭的:“视之不见名曰微,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夷。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老子》第十四章)然而,道的无形无象并不是绝对的空虚,而是实存的东西:“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第二十一章)[21]
宗先生显然是比较偏重出于老子的这种对道的解释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的后半部分所探讨的各种艺术形态——绘画、书法、舞蹈、诗歌、音乐、建筑——在宗先生的笔下,无不是对道的体证与观照。
其实,宗先生更加在意的问题是道如何贯穿于中国艺术意境的诞生。该文在讲到道这一形而上原理时首先引用的是《庄子》里庖丁解牛的寓言,说明“道”与“艺”的关系,以及“道”是如何寄予“艺”,或者说,“艺”是如何创生于“道”的。
道为什么能够作为中国艺术意境诞生的形而上原理?或者换一种问法:“道”与“艺”的关系如何?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句话是很精辟的。道通过艺术家的把握并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艺术的意境便是对道的直观的具体的表现,是道的一部分。朱熹就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朱子语类》)
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先生提出文以载道的说法,《通书·文辞》中有言:“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者佳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好一个“艺焉而已”!仿佛文艺只有成为说教的工具才有价值,就像车的价值在于载物一样,文的价值在于载道。周先生未免过于功利了。要知艺术意境的诞生是与功利没有什么关系的。
说明道与中国艺术的关系,《庄子》中还有另外一则有名的寓言:“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这则寓言中,玄珠象征道,知象征理智,离朱象征视觉,吃诟象征言辩,象罔则象征有形和无形、虚和实的结合。只有象罔才能找到道,也就是说,道是通过象罔来体证和表现的。无形无象,不可捉摸的道恰恰是在于形象之中,只不过这形象不是一般的形象,是有形与无形相结合的象罔。这象罔也就相当于艺术意境。
宗先生进一步提出“舞”:“只有活跃的具体的生命舞姿,音乐的韵律,艺术的形象,才能使静照中的'道’具象化、肉身化。”[22]这里提示我,中国艺术意境的诞生就是道的具象化和肉身化的过程,而这道成肉身的过程是由“舞”来实现的。“舞”可以说是生命的律动——也就等于道的律动——它包括“生命的舞姿”,“音乐的韵律”,“艺术的形象”三个方面。这“舞”舞出的是道的节奏。这让我看到了中国艺术意境的生生不息的活力,它并不是对道的模仿,而是在道中舞动,直接呈现道,或者说,呈现道的律动。
“尤其是“舞”,这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律、功、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表现的究竟状态,且是宇宙创化过程的象征……艺术表演着宇宙的创化。”[23]这话不如改成“艺术表演着道的节奏”。宗先生在另一段话里说得更加直白:“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24]这话也道出了另一个事实:中国的艺术正是以道作为自己意境的形而上基础,才具有深度和灵魂;而道也正是因为艺术才能以活跃的生命形象展现。
接着,宗先生直接从“舞”讲到了“空”,讲到了各种艺术形态中的“空”。从“舞”的提出到“空”的发现,是需要一点艺术的想象的。“由舞蹈动作伸延,展示出来的虚灵的空间,是构成中国绘画、书法、戏剧、建筑里的空间感和空间表现的共同特征,而造成中国艺术在世界上的特殊风格。”[25]这“空”也如前文讲到的“道”一样,其表示的并不是“空洞”或是“空虚”,相反,是活跃的“空灵”,空灵之境也便是意境了。“虚空中传出动荡,神明里透出幽深,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是中国艺术的一切造境……中国人对'道’的体验,是'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唯道集虚,体用不二,这构成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和艺术意境的实相。”[26]
做一个不是很恰当的类比,对于中国艺术意境来说,其形而上的范畴中,“道”是本体论的,“舞”是方法论的,“空”是认识论的。无论是“舞”还是“空”,在本体论的意义上,都是“道”。“道”便是中国艺术意境诞生的哲学基础。

文心 诗情 博物 乐境
青少儿人文美育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