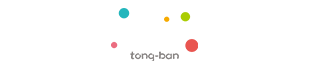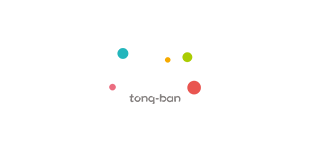在 《中国审美意象论的发生学进路及其现象学诠释》中,我提出了中国审美意象论也是感性学的体验论,其发生学路径是源于解决“言—意”关系问题的论争,即儒家 释“意”为“志”的基于“言—志”的对称结构关系和道家释“意”为“道”或近“道”的基于“言—道”的非对称结构关系的分歧,因应这个分歧,先秦学者引入 “象”论;这个“象”论又经历了从“实象/物象”到“易象/拟象”再到“意象”的演变;在意象概念形成后,中国艺术遂得以克服主客裂变而实现了带有意向性 特征的客体形式在主体意识活动中的图像化表达,打破了能指/所指的二元对称结构,发展了其注重“意向性”的优长。这种意向性让诗人或艺术家得以在假象/取 象中建构某种超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维时间和空间交织的边缘域。实现了对于“实体论”和“认知论”的消解。由此出发,有学者将西方古典形而上学美学视作 “实体本体论”的,而将中国的意象论美学视作“现象本体论”的。这种关于“审美意象”的“现象本体论”的提法是否成立,是否独属于中华美学,将是本文探讨 的重心,笔者也将借此分析学界有关中国美学的现象本体论的建构、困境与出路,并进而对中国审美意象论做一个现象学的考察。

“美”
一、意象:建构一种现象本体论的尝试
郝 大维和安乐哲在《通过孔子而思》中指出:“儒学却表征为现象本体论,而非实体本体论……儒家不考虑抽象美德的实质,他们更关注对特定语境中个体行为的诠 释。”认为盎格鲁—欧洲哲学内部对“实体性自我”观念的种种批判或肇始于尼采,而突出表现在20世纪詹姆士、柏格森(Bergson)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 上,但这种改变需要借助外来文化,因为盎格鲁—欧洲思想的理论环境并不是非实体主义思想的最佳表达。郝大维、安乐哲继续指出,作为孔子思想基础的现象本体 论主要着眼于内在宇宙“秩序”及其“创造性”,孔子思想的秩序不是源于已定模式,而是来自于过程并被实现的。
对于这 种“现象本体论”,美学家朱志荣也称其为“动态本体论”,并认为中国美学家强调动态本体论(现象本体论)的美学思想从先秦以来已获得充分发展。在朱志荣看 来,早在《易经》中,“象天法地”的“尚象”思维就成为中华美学现象本体论的肇始。这也就是《周易·系辞下》所阐发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 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种取象天地的现象本体论美学建构,注重物我关系的相互激发,“感 者动也,应者报也,皆先者为感,后者为应”(孔颖达《周易正义》),消解自我主体的执着,即孔子说的:“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 罕》);强调非实体性的虚静其心,即庄子说的:“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庄子·天道》)

郝大维、安乐哲著《通过孔子而思》
在 以先秦儒、道两家为奠基的中华美学统绪中,这种强调没有前定实体性自我的动态本体论或现象本体论对后世艺术创造产生深远影响。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 “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马祖道一:“心不自心, 因色故有。”《文镜秘府论》引王昌龄之语:“感兴势者,人心至感,必有应说。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柳宗元:“美不自美, 因人而彰。”范晞文《对床夜语》:“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王夫之:“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这都强调了“随物”“与心”“缘 色”“感会”的因缘生发,不存在“美”的实体本体,一切皆处于有待实现的动态过程之中。
朱志荣所提倡的这种现象本体 论或动态本体论,在当代美学家那里似乎也得到了体现,就是注重艺术意象所呈现的内在宇宙创造性特征与外在宇宙的生生不息相呼应,是一种生命瞬间生发的美感 体验,这就如朱光潜所指出的:“ 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宗白华也强调这种艺术意象与万物的通化感应关系:“象如日,创化万物,明朗万物!”叶朗同样否定实体化的美,而提出“美在意 象”说,认为:“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外在于人的‘美’”,“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纯粹主观的‘美’”,阐明美是动态的即时生成的,是“如所存而显之” “显现真实”,这不是柏拉图的“理念”或康德的“物自体”这样的“实体”,而是动态存在的“真”,是胡塞尔说的“生活世界”,是中国美学说的“自然”,是 对自我的有限性和物的实体性的超越,是立足于天人合一的对于主客二元论的超越。
朱 志荣提出的“美是意象”说,看似为不可思议,但从上面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现象本体论或动态本体论的历史描述,以及从朱光潜、宗白华、叶朗等的致思路径入手, 就不难理解朱志荣提出“审美意象”的“动态本体论”的着眼点在于强调中国人的审美思维是动态的实践的,在于强调中国人的审美活动的过程就是意象创构的过 程,并希望揭示意象创构中的感物动情是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物我互动和交流。然而,这里的难点在于,“美是意象”说以及“审美活动的过程是意象创构的过程” 是全称判断式表达,这就会涉及非中国或非东方的他种文化的审美活动是否也是如此的问题?说意象创构中的感物动情是以天人合一为基础,这显然是立足于中国美 学的,但前面既已说明审美活动就是意象创构,就是不是又将其他文化的审美活动也包括在内了?
朱志荣“美是意象”说既 是对于叶朗“美在意象”说的进一步发挥,是期望对中华美学的现象学维度做出一种本体论的诠释,是当代中国美学人适应西方美学话语又强调中华美学独创性的观 念调和。这种说法重视中华美学中的美是体验,不是西方认识论模式中的“主客二分”,但其关于“美”是“天人合一”的存在论模式,却已有学者明确指出其问题 所在,认为审美体验未必就一定发生在“天人合一”的模式之中,在西方“主客二分”的二元论思维模式中,其关系并不是天人合一的模式,但审美同样在发生,当 主体面对客体时,他好奇、紧张、征服和皈依,他因失败而悲壮,他因荒诞而滑稽……主与客并未走向物我浑融,而是始终在复杂的关系中搏斗。这不是东方的意象 美,却同样是另一种美。
综上可见,无论叶朗的“美在意象”,还是朱志荣的“美是意象”,其贡献主要在于以“意象”为 线索,对中华美学非形而上学、非认知论的体验性特征进行了历史梳理和理论把握,但其从“意象”出发建构的现象本体论或动态本体论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其关键 就在于扩大化论述,即他们首先确认“意象”是中华美学的独创概念,其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强调非实体论的动态性瞬间性生成,又得出“意象”是美的“本体” 这样一个普遍性结论,这就将西方形而上学的实体论美学及其美感体验也包括在内了,他们既说明西方古典美学是实体论和主客二分,是非意象化的,却又根据中国 古典美学经验得出一个“美在意象”和“美是意象”的结论,这就自相矛盾和以偏概全了。这样一个矛盾和困境是无法从叶朗和朱志荣先生的命题和学说中解决的, 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思考路径。
二、意象作为美的本体言说的困境
“美 在意象”和“美是意象”的命题之所以偏颇,是因为主词“美”是一个大概念,限定它的宾词却是一个小概念,这就像说“水果是(在)苹果”“人是(在)男人” “女人是(在)美女”一样是不妥的。因为美不仅在意象,美也在形象、在结构、在形式、在韵律。叶朗、朱志荣仅仅因为强调中国艺术的美和美感体验是动态的, 就做出“美在意象”和“美是意象”的判断,忽略了西方美学也可以引伸出来的“美是典型”或“美是形象”“美是理式”的命题。我曾经著文指出,中国文学艺术 中的“形神”或“意象”得到了更充分的阐发,是因为在“形神”思想中,“神”因其让事物脱离了质料特征而具有了超越化和空灵化特征,更契合了中国人的非实 在化观念。“意象”美学则有两个方向,一是内涵的“意”因其自我化和主体化的“以我观物”思维契合了中国以儒家为主导的抒情诗学发展路线,二是因为内涵的 “象”因其非主体化悬置自我的“以物观物”思维契合了以道家为主导的自然诗学发展路线。
相对说来,中国文学中另一个 被忽视的关键词“形象”既有着对“神”之超越向度的摒弃,又有着对“意”之主体化维度的疏离,在西方文学中却得到了更大程度的重视。相较而言,中国美学重 传神,重意象,西方美学重理式,重形象。这种形象创造具有外在形式的可感性和丰富性,又具有内在质料的凝重性和实在性。在近代以来,西方文学更是在典型形 象塑造中带领世界走向了一种表象化的创作道路,中国近代文学艺术受西方影响,那种原本注重内在化创作道路的意象美学也被这种世界潮流所波及,开始注重外在 化表象创作方向,也就是形式和质料结合的实体化的创造。
叶 朗“美在意象”说、朱志荣“美是意象”说可能导致两个误区:一是模糊了“意象”和“形象”的区别,将“美”当作被认识和研究的外在对象;二是研究“意 象”,实际是希望研究“美”本身,这就必然落入柏拉图式“美是理念”的本体论套路,但因为神或理念不可说,故必然导致苏格拉底的“美是难的”的本体论美学 难题,并将在和基督教神学美学接轨中导致对上帝独一之美的绝对推崇和对于自然艺术之美的否定。中国美学中的“形神”“意象”注重以形写神,因意设像,却并 不预设绝对独一之美,那种朝向“形象”的造型化实在化的艺术创造也不甚发达,中国美学中的“神—形”张力并未被推到极致状态,作者的“意”所投射的“像” 而构造出的“意象”就并未朝着“美的本体”(理念)过度伸展,也未朝向“美的造型”(形象)进行淋漓尽致的发挥,这既是中国美学的优长所在,也是其缺点所 在。
叶朗、朱志荣等将美的本体预设为形而中的意象,这隐藏着与西方学术接轨的良苦用心,既希望借助意象概念开显出一 个美的本体(近于理式)的形而上维度,又希望外化出一个美的造型(近于形象)的形而下的维度,以克服中国古典美学张力不足、清晰性不够、概念界定不明确的 弊端。于是,既有形而上(意近道)又有形而下(象近形)的“意象”概念就成为其构建中国美学学科的最佳切入口。这种美的本体预设所隐藏的美的造型化诉求, 虽未被朱志荣明确提出,但却隐藏在“美是意象”的动态本体论中,看似否定了形而上的绝对性和形而下的外在性,但因本体和现象所隐含的对举关系,就已经有将 “美”引向形而上学的概念知识和形而下的客观知识的双重偏弊。
这 种借用西方本体概念以诠解中国美学,往往会沦为亚里士多德“存在之为存在”的“本体”观的注脚。中国思想中有“本”和“体”两字,其日常语义就是生物(植 物或动物)的主要部分。自西汉以来,人们逐渐习用“体”“用”概念,魏晋之际,“体”“用”问题讨论日趋成熟。而该时期出现的“形神”概念和“体用”概念 相通。六朝隋唐年间,往往将“本”与“迹”相对,可谓体用的变例。现代学者将魏晋玄学释为本体论的,实际与魏晋玄学的“体用本末”概念并不吻合。西方本体 概念主要与知识论和逻辑学相关,是从现象与本体两分角度展开的本质主义思考方式,其本体趋向于实体,其基础是“主客二分”,中国思想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古希 腊形而上学(metaphysics)或本体论(ontology)思想传统,而是讲究本体不离器用,是“主客混冥”或“天人合一”,强调无名,超绝名 相,不落言筌。
西文语境中的美学最初也不全是形而上学和知识论的概念,其本义就是感性学。近代以来,感性学被窄化为 美学,这实际是对感性学进行狭义取舍后的学科定位,是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古典形而上学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知识论的霸权话语在诗艺领域的强行介入,是诗 艺研究未能自觉从其自身寻找合法性的信心不足的体现。自从柏拉图以来,截然划分本体与现象的主客二分哲学就主宰了西方美学,“美”就被视作本体或客观存 在。这样,当中国学者思考美学的学科定位时,就沿袭了西方美学将美的本体论预设为美学学科存在基础的传统,就将中国诗艺领域的意象放到美学的学科范围来考 查,就作出了“美学”是研究“美的本体”和“意象”是“美的本体”这样一个嫁接。于是,“意象”作为中国艺术中具有发生学和现象学维度的概念,就被转变成 了一个符合西方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和主客二分的知识论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像
中 国传统诗艺不仅不存在意象是“美的本体”的问题,而且“意象”也是“跨学科理论”的存在,既非独属美学,也不能被美所限定。然而,现在“美学”却将“意 象”圈进自己的学科疆域,并指定其就是美的。这样,当叶朗和朱志荣提出“美在意象”“美是意象”的命题时,就可能只是通过某种诉诸历史话语的神圣言说以实 现对美学的学科权力的合法性建构,以让意象成为中国古典美学学科的基础性概念。显然,原本应当用跨学科手段来研究意象的道路就被阻断,研究艺术的感性存在 状态和发生过程的联系就被截断。回到感性本身,就是我们联系起“意象”和“感性学”的道路和桥梁。
于是,在朱志荣这 里,就存在着中西理论嫁接中的矛盾与困惑,当他说“意象作为美的本体是动态生成的”时,他实际沿用了源自西方美学中的“本体”概念,即本体的绝对性、永恒 性与静止性,但他们现在却提出了“动态本体”的说法,试问,既然是动态的变化的,又如何可能是绝对的永恒的,本体如何动态变化?在“意象”概念中“意”和 “象”的关系上,朱志荣也提出了“创构”论的说法,认为“创构”论就是注重过程体验的,然而这种对过程体验的注重又是与其将“意象”放入“美学”的前提设 置和“美”的“本体论”预设构成矛盾的,故虽已思考意象的创构过程,却难以在非本质化的“意”“象”及“意—象”关系如何可能的道路上再往前继续推进。这 样,我们就看到,从朱光潜、宗白华等老一辈学者引介西方美学以建立中国美学学科以来,中国美学人就始终存在着一个如何界定“美”的难题。于是,追寻“美” 的本体以适应形而上学哲学,研究“美”的客观知识以适应认识论哲学,就成为中国美学学科建设的方向所在。但这也造成严重后果,那就是具有东方思维特征和独 特情感体验的中国艺术精神就被本体论和知识论所切割,就导致了中国美学的失语症。
但朱志荣的贡献也是突出的,那就是 当他谈到“审美意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时,就可能是希望将艺术的感性体验提炼为美,并进而由现象美和艺术美上升到理式美,这也体现着中国美学家适应西 方形而上学美学概念的学科自觉。他后来继续谈“美是意象”,就有着将西方的形而上学难以证实的理智之“美”化入中国可以觉知的感官、行动和实践过程的用 心,有着从本体论走向生存论的进路。然而,当限定了美学的本体论预设这样一个狭窄视域,中国美学人大多也只能从物我交融、情景融合、主客合一的形而上学的 语境来展开,从而忽视了中国古典意象思维的发生境域最初并不是为了摹仿现实/客观世界或是追寻本体/理式世界,不是诞生于某种现象和本体对立的二元预设或 “意”和“象”相互符合的主客关系,而是诞生于注重解决“意—言”的语言符号是否能有效表达作者情意的问题和意向性生成的抒情话语传统。
三、意象在现象学视野下的发生学诠释
“意 象”主要诞生于中国思想家关于“言—意”关系问题的思考,它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者所认为的是从西方美学借用的概念,也不是钱钟书等所说的晚至明代 才盛行的概念。中国思想家集中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以“言”达“意”?从“意”到“言”如何显现?在先秦儒家那里,最初存在着一种关于“言—志”的对称性因 果结构关系,如《论语·先进》载子路、冉有、公西华、曾晳各言其志趣,孔子以为“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论语·子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这里的“志”有小大,却都指向具有“善”的本质的正面理想。在孔子那里,“意”带有一种私人性、模糊性和狭隘性,如“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而“志”则具有清晰性、公开性、一元性,并可明示于天下,于是有了“言以足志”的说法,而这“志”又约束“言”,如《孟子·万章上》:“说诗者,不以文害 辞,不以辞害志。”这实际某种程度上预见到“辞”和“志”的距离,而在阅读中,对于读者私人性的“意”与经典中普遍性的“志”的关系问题,孟子提出了“以 意逆志,是为得之”。这涉及到个体性如何去介入公共性的思考,只是未能深入,还重于批评修饰性的“文”害“辞”,华美的“辞”害“志”问题,强调读者摒弃 个人性的“私意”去回溯经典化的“善志”的问题。于是,《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就是延续孔子、孟子传统的“志—言”关系 论,提倡的是“志之所之”,而非“意之所之”。

孔子与弟子“农山言志”
问 题的转变是在先秦道家思想者那里,道家思考的核心问题恰好是儒家否定或搁置的非公共性和非知性的“意”的问题,他们明确认识到“意—言”的非对称结构关系 及其表达困境。如《庄子·秋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这实际可看作是对《老 子》开篇的“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的深化阐释,是说明“言”和“意”都只能达致“有形”之物,“言”能论“粗”,“意”可致“精”, 其关系是非对称性的,但都远离着“不期精粗”的“道”。只是“意”更接近“道”,不是可以明言的,如《庄子·天道》:“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 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这就指明了“意之所随”是“不可言传”的, 是个体生命最内在化的通于宇宙天地的神秘体验,不但是不能否定的,而且是高于儒家注重言传的“志”,儒家之“志”属于人道,而道家之“意”却紧随“天 道”,《庄子·外物》就几乎将“意”与“道”同等看待:“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这样,“书”“语”(言)就属于可见 的有形层次,而“意”“意所随”就属于不可见的无形层次。而这也是儒家重人道之可见与道家重天道之不可见的分歧。
我 把道家所重视的“意”看作是现象学所说的“非对象化”的“自身亲熟”的“原意识”,看作是弗洛伊德说的“潜意识”,它更接近生命的基座和底层,是天地万物 得以通联的生命潜流。道家的勇气就在于对这种看起来属于私人化和个体化,却实际是弥散于生命体中的具有“大公共性”的“意”或“道”的反观,是将具有“社 会公共性”的“志”放回其具有“自然公共性”的“意域”或“道场”。于是,儒家的“志—言”对称结构关系就被道家的“意—言”非对称结构关系颠覆了。但显 然,道家既然将具有大公共性的“意”和“道”放入反思领域来观照,那就必须找到合适的媒介或触发点将其勾引出来。而儒家面对这种难于辩驳的更大公共性的质 疑,就得找到让社会性的“志”可以回溯自然的“意”的途径。这样,一场可能是介于儒家和道家之间的经典对话就发生了:“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然 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周易·系辞上》)《易传》借孔子以引用“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的说法,就可能是重述《庄子·天道》篇“世之所贵道者,书也……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的挑战,而后再提出“立象以尽意”的解决途径。这里的“立象” 就是指《易经》的“卦象”和“爻象”,不是自然世界的“物象/实象”,而是“现象/形式”在主体心镜或意识活动中的图形重构。故有“易者,象也。象也者, 像也”(《周易·系辞下》),“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周易·系辞上》),以“像”释“象”,说明易传作者认为 《易经》的创作就是借助物象的形式“像”以在意向性活动中重构“易象”图式,是假象和虚象,是解决“意—言”非对称性困境的尝试。圣人作易就是从“象”到 “像”的取象和象征,就避免了寻找不可知的物自体、实体、客观本体的偏执,避免了“本质/现象”完全对称的因果关系和必然预设。《易传》对《易经》的“立 象”阐释突破了“言→意”或“意→言”的线性思维图式,而成为一种缘构发生式的活动,并有近于现象学的意向性审美体验。于是,“意”不再等于名言概念或观 念客体,“象”也不是实在客体和事物形象,而是介于“不可见/可见”“未定/已定”的“像”,是介于“意”和“言”之间的交融域,是受着“互渗律”原则支 配的,即现象学所说的“意象性客体”。

《老子骑牛图》(明 张路)
另 一场发生在道家和名家之间的经典对话同样可看作是从社会性的“志—言”对称性结构到“意—言”的非对称性结构的返回:“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 ‘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不 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秋水》)在这段文字中,庄子说的“鱼 乐”,实际上只是他此时的愉悦心境和自由体验借助鱼在水中游动的“现象形式”在他自己的“言说”中的构图成像(意象),“鱼乐”是属于庄子自我生存体验的 建构,并不属于知识论的可验证和逻辑学的推理范畴。惠子对庄子的否定蕴含着三重意思:鱼乐是否存在(什么是鱼乐);即使鱼乐存在,又怎么可能认识(如何认 识鱼乐);即使能够认识,又怎么可以用语言来表述(怎么会说出鱼乐这样的话)。惠子就将“鱼乐”放到形名之辨的逻辑学和认识论范畴,即假设作为自在本体的 “鱼乐”(意)存在与同样作为自在本体的“我”(意)的并存,当两个自在本体并存时,本体因其是自在自足和静止圆满的,遂也是不可能相互通达的,当我们说 “本体”时,实际就有近于莱布尼茨所说的“单子”。但庄子反对这种将个人体验导向本体论和认知论的思维方向,而是主张将个人体验引向现象学和生成论的方 向,因为无论是将所谓“鱼乐”还是“我乐”导向“本体”,就会遮蔽其实际只是作为当下“现象”的过程化体验,就会发现认知静态本体的“意”(鱼乐、我乐) 和以认知为基础的言说方式都是不可能的,庄子所说的“鱼乐”实际是庄子之乐(意),是属于当下体验的感兴之会,就因缘牵系状态中的触物兴感或感物兴情, “鱼乐”实际不过是“庄周之乐”的意向化表达和构图成像的隐喻,“鱼乐”就是建构的一个生命意象。
然 而,在从朱光潜以来的学者论述中,意象却被作了客观化的解释。如朱光潜在《诗论》中就视“意象”为审美对象,是相当于“景象”或“表象”的情景交融的景, 这是外在化的。叶朗《美学原理》认为“意象世界显现一个真实的世界,即人与万物一体的世界”,这是客观化的。朱志荣《审美理论》认为“审美意象中包含了主 体审美活动的成果,主体与对象的审美关系最终凝结为审美意象”,“审美意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这是本体化的。彭锋在阐释“濠梁之辩”时也做了认知哲 学和生活哲学的区分而把知鱼乐视作“以此知彼”的符合论与反映论,这是认知哲学的。各位美学家在探讨“意象”时,都承认了某种外在客观的东西,都未能将他 们自己已经认识到的某种体验论和现象学思维贯彻到底。虽然叶朗谈到“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外在于人的‘美’”,“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纯粹主观的 ‘美’”,但他提出“美在意象”时,仍旧采用了本体论和认知论的表达,落入了客观主义的思维窠臼。
四、意象思维是一种化感通变思维
从 前文论述可以看到,无论是将中华美学看作本体论、现象本体论或动态本体论的,其中都隐藏着难以克服的危险,就是将注重现象学和发生论的中国美学导向形而上 学和认知论维度。虽然有学者将叶朗“美在意象”说看作是对蒋孔阳“美在创造中”的继承,但“美在创造中”却更契合中华美学的生存论和体验论特质。“美在意 象”或“美是意象”,却导向了本体论和认知论方向。于是,当成中英指出:“中国美学是一种本体论性质的美学,本体论美学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审美传统之中。” 这不过就是用西方的本体论和认知论思维来切割中国美学了。当朱志荣赞扬成中英把握到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时,这也其实表明了他要建立本体论美学或形而上学美 学的用心。
叶朗、朱志荣在将中国美学界定为本体论美学方面误入歧途,但在探讨中国美学意象思维方面却有发人深思处。 比如,叶朗认为,中国传统美学的艺术本体就是“意象”,而意象的基本规定就是情景交融。朱志荣赞扬成中英所说的中国美学的观与感的统一,认为成中英所说的 “观”“感”“思”“觉”“通”的过程特别适合诠释审美活动,认为意象的创构是主体以刹那间忘我的“虚静”之心去顿悟对象,是老子说的“涤除玄鉴”,是禅 宗的“心如明镜台”,是朱熹的消融心灵渣滓。这都涉及意象构建的思维方式问题。但只是“情景交融”和“虚静”的说法,并不能很好地概括意象思维的发生过程 及其哲学基础,我们仍有必要回到意象思维的发生学背景以对其做出现象学的诠释。
在 叶朗看来,道家老子哲学有两个基本思想对中国意象论美学影响甚大:第一,“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命,对于一切具体事物的观照(感兴)最后都应该进到对 “道”的观照(感兴),这也就是朱志荣称赞成中英所提出的中国美学意象创构中的“观”“感”。第二,“道”是“无”和“有”、“虚”和“实”的统一, “道”包含“象”,产生“象”,但是单有“象”并不能充分体现“道”,因为“象”是有限的,而“道”不仅是“有”,而且是“无”(无名,无限性,无规定 性)。就“道”具有“无”的性质来说,“道”是“妙”。这里关于“无”和“有”、“虚”和“实”的关系就涉及到朱志荣称赞成中英所把握到的中华美学意象创 构中的“觉”和“通”的问题,从有以觉无,觉有无之可通。
成中英、朱志荣在探讨意象思维方面极富启发,但“观” “感”“思”“觉”“通”,可以描述思维过程,却还未能上升到如“意象”这样的关键词的高度,笔者尝试借用道家思想视域中的“物化”概念和儒家思想视域中 的“物感”概念来构建“意象”美学的根本思维方式“化感通变”思维。这种化感通变思维我们可先借用庄子《齐物论》中蝴蝶梦的“物化”寓言来予以阐释: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庄周梦蝶》(当代 范曾)

《庄周梦蝶》(明 陆治)
“庄 周梦蝶”已然成为中华美学的一个经典意象建构,庄子最终着落于“物化”以释梦,“物”关乎《齐物论》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天人同构和万 物同根问题,万物各不相同,为何能同根同构并生齐一,这就是因为能够“化”,无论鬼、神、人、物都可相互转化,因万物相“化”,故万物相“通”,庄周梦见 自己变为蝴蝶,是隐喻万物既可相化,则可相“感”,就是“感”“觉”到自己可化为蝴蝶,蝴蝶可化为庄周,万物皆可化感或通感。然而,梦醒之后,又发觉在现 象世界,庄周自是庄周,蝴蝶自是蝴蝶,二者之差异湛然分明,这就是从本根化通之道而演绎出的现象之“变”。只有至人或圣人能觉悟到万物本根相化相通的真 谛,感知到万物现象差异常变的虚幻,这就是庄周梦蝶这一经典意象所隐藏的化感通变思维方式。承论本根相化相通,就消解了本体的一元和静止;承认万物现象的 差异常变,就消解了现象的客观性和外在性。这就是在“有—无”“虚—实”中游走的庄子所说的“两行”之法,也就通于后来佛教禅宗的“双遣”的“性空幻有” 的“中道”方法,这也是我提出的庄子“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的寓于道体于生活的“庸道”思维方法。
这种意象美学建构中的“化感通变”的思维方法还可借用《毛诗序》中的“感物”(物感)思维来予以阐释:
《关 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 言……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 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 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关雎图》(当代 于水)
《诗 经·关雎》篇中的雎鸠和鸣与君子求淑女是相互关涉和隐喻的意象,《毛诗序》的诠释先从自然之化开始,而引入人文教化,这里最重要的是万物的本根相化是人文 教化得以可能的哲学基础,因为这化,而后才有万物的相动相感,“风以动之”,“动天地,感鬼神”,才有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对于人心的不同感动, 先王之政所以美,就在于体察到了自然和人伦的相化相感而能顺导之,故得以政“通”人“和”。然而后世之人不明先王之道,而后有“国异政,家殊俗”,这是 “变”,在艺术上就有了“变风变雅”。而这就是“化感通变”思维在从《国风》到《大雅》《小雅》《颂》的实际运用。这种思维就不能简单地归纳为天人合一, 这里的“意象”创造如《诗经》的“黍离之悲”“东山之叹”,还有《楚辞》的“洞庭木叶”“行人悲秋”,都是天人不和谐、神人不和谐、物我不和谐而造成的强 烈“悲情”,这就与《关雎》篇所代表的正风正雅的天人合一、两性和谐、家国和谐不一样了,而这也就否定了宗白华、叶朗、朱志荣所说的中国意象美学的哲学基 础是“天人合一”的说法。


《雎鸠》(日 细井徇)
这 样,我们就建构出中国意象美学所内蕴的化感通变思维方式,就指出从老庄到佛禅的“以物观物”的“无我”之境,就有了虚去自我主体的“损道”思维,就是庄子 的“吾丧我”“心斋”“坐忘”,是佛禅“诸法无我”“无念为宗”,就否定了将现象实体化或本体化的倾向,如庄子的鲲鹏互化、庄周梦蝶,佛禅的“诸行无常” “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庄禅美学的意象创构就既在理想维度上提倡天人合一,又在艺术创作上虚去物我的实体而实现了天人合一,故其创作的意象唤起人的美 感是冲淡平和,如澄明之镜可映照万物。这种“以物观物”的意象创构在陶渊明那里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冲和至境,在 其中,万物所蕴含的时空差别被最大限度地消解。
同样,我们也指出了在先秦儒家影响下的后世文学艺术的“以我观物”的 “有我”之境,就有了以君子和士人的家国情怀投入政治生活的用世之心,其在理想维度上仍旧是提倡天人合一的,就是孔子、孟子推崇的圣人垂衣裳而天下治。这 里的圣王之治已经有了衣冠礼乐的人伦秩序,但这秩序被认为是效法天道自然的,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象天法地”的创造,是所谓“大乐与天地同和,大 礼与天地同节”的天人通化交感,但时移世易,“国异政,家殊俗”以后,就有了天人秩序的混乱,就有了“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周易·归妹·彖》),这 时诗人创构的意象就是天人分裂或主客不和谐中的强烈主体情感借万物形式所做出的意向性建构,就有了陆机诗的“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赴洛道中 作》),江淹的“行子肠断,百感凄恻”(《别赋》),钟嵘的“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诗品序》),李煜的“问君能 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这都是在感受到生命归于大化(与万物迁化的死亡)却又人生不遇中所触发的物感(我伴随万物纷落的感伤)悲 情,是包孕着极强情感的意象创构,这其中呈现着将断裂的空间秩序化入有限的个体生命和家国生命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的自觉。
综 言之,叶朗“美在意象”、朱志荣“美是意象”的说法,都有着对于现象学方法的借用,有着对中国“意象”的“动态”和“空灵”的关注,但其论述方式却是已然 式的,即描述或界定意象的特征,仍旧属于西方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路径,而对于“意象”作为概念是如何发生的,其艺术创构是如何实现的,还缺少深入细致的考 察。朱志荣将“意象”看作“审美本体”,认为这种审美本体是“动态生成本体”,这都只是描述其所说的“意象”的特征,其中充满了矛盾,如果本体是生成的, 那现象同样是生成的,本体与现象的区别又何在?“动态生成本体”实际已经混淆了西方“本体—现象”作为对立概念的分歧和差异。而且叶朗、朱志荣将“意象” 创构的哲学基础看作是天人合一,这也是与中国意象美学的实际状况不相符合的,从庄禅路线的以物观物的意象创构确然是天人合一,达到了自然的化境,从儒家路 线的以我观物的意象创构却是乾坤失序人道混乱中的悲情体验的创造。意象思维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化感通变思维,这也是为本文首次所揭显,它很好地解释了意象创 构的发生学路径,让我们可以回到中华美学的历史现场,以创建中华美学的独特理论话语,为当代世界美学提供中国经验。

文心 诗情 博物 乐境
青少儿人文美育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