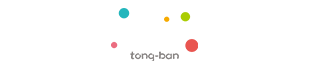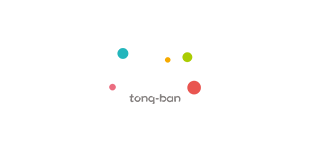无论从艺术层面还是社会现实层面来看,“乐”都可算作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概念。一方面,它作为最早成熟的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密切参与了古代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建设。较之诗文、绘画、书法等后起的艺术,“乐”早在上古时代便已发展起来,它“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吕氏春秋·大乐》),是顺应天地自然的变化规律而成的,也能够促进天下太平、万物安宁,一切顺应正道。因此上古帝王们便纷纷制乐,用于祭祀典礼或宣扬功绩。孔子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一个根本原因便在于诸夏之国有礼乐文化,从而能够确保社会文明有序。自春秋以来,“乐”更成为了士人素质培养和境界提升的必要手段,即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另一方面,“乐”发挥效用的本质是一种流动性的艺术审美经验。它产生于自然之道,但这种自然之道毕竟需要人的主观把握才能彰显价值。因此《乐记》提出:“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人心感物”说明乐的本质既不是客观自然,也不是主观经验,而是主客交流。在古人的哲学观念中,主客二元绝对不是平等对立的,古人寻求的是将“小我”融入到“天地大我”的境界之中,而这正是“乐”所能解决的问题。正如《礼记·乐记》所言:“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与礼法相比,乐的作用在于使人“合同”以及“相亲”,这是对礼法所强调的人与人之间身份区隔的一种弥补,也是对人与世界万物关系的一种整合,引导着个人对于社会现实和宇宙秩序的审美认同。
周王朝衰败以后,乐官散于四方,古乐逐渐式微,到西汉时已经完全失传,音乐的社会性以及交响性逐渐让位于曲高和寡的个人独奏。但乐的节奏、韵律和美学宗旨却构成了中国诗、画、舞以及书法、建筑等艺术的内在精髓,成为中国文化艺术民族性的独特表达方式。
因此可以说,从文化价值、社会影响以及学理意义上来看,对于“乐”的研究都是极为重要的。然而,文献的零散、“乐”本身的复杂内涵以及音乐与文本之间的距离等因素,都阻碍着研究的深入,也使相关问题一直未能引起太多关注,这一理论空场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为数不多的理论成果中,韩伟副教授的《宋代乐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提供了诸多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可视作乐论研究的成功探索。
该书共六章,按“本体论”和“关系论”两个层次展开。前三章以“乐论”理论本身为核心,分别探讨了宋代乐论对前代乐论的接受和新变情况、宋代乐论“形”对“义”的本体性超越、宋代乐论的经典化三方面的问题,完整地呈现了宋代乐论的理论建构过程。第四至六章则结合具体个案,分别探讨了俗乐和民间乐论与宋代主流乐论之间的背离、宋代乐论与文学思想之间的互动、宋代乐论对于文学创作实践的影响等问题,考察了宋代乐论对于雅俗文艺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该书对于宋代乐论的全面考察,既理清了乐论在宋代的继承和发展状况,呈现了宋代乐论的独特风貌,也为文艺理论研究、美学研究乃至文学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和参照。在我看来该书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研究对象上,对于“宋代乐论”的研究具有时代和对象的双重意义。一直以来,学界对乐论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先秦,因为先秦是古乐发展繁盛的时代,《礼记·乐记》、《乐论》、《吕氏春秋·古乐》等文献也是影响深远的乐论经典。除先秦乐论研究以外,对乐的研究则又多集中在各朝代乐制,也就是用乐方式、机构设置、乐队规模、乐器使用等方面的研究上,对于“乐论”本身的研究则较少涉及。而宋代是中国文艺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雅文学内部除正统诗文之外,词曲拓展出了一片新天地;而在更大的范围内,雅俗文学逐渐交融,民间文艺开始繁荣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乐”实际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关于乐的理论和丰富实践,在潜移默化中推进了宋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转型。以此为思路,作者首先将“乐”区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是雅乐及其理论层,也就是古典意义上的“礼乐”之“乐”,它既承载着天人沟通的观念,也蕴含着“成于乐”的儒家最高美学标准。第二层则是具体的“音乐”之“乐”,指实际的用乐和俗乐。这一层面的乐表现出的是对于音乐的实际使用,更突出纯粹的音乐性和形式美。作者指出:“宋代是传统乐论经典化时期同时也是古代乐论开始形式化的转变时期,因此乐的两种含义在很多人的理论中还不是泾渭分明的,处于一种相互纠缠的状态。”(第5页)但也正因如此,这两层区分又是更加必要的。礼乐之“乐”更偏重意识形态性,而音乐之“乐”则更偏重审美性,如果说乐是依靠前者而确证自身合法性的话,它又是凭借后者而保持长久活力的。宋代乐论正是对这两层面的充分继承和有效激活,因此只有将这两个层面做出区分和完整考察,才能更好地把握“乐”在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作为一种特殊审美意识形态的鲜明属性。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该书将文献梳理、文本阐释和文化研究勾连起来,宽阔的研究视野使结论更加充实可靠。如上所言,乐本身可区分为礼乐之“乐”和音乐之“乐”,所以对于“乐论”的考察研究也需要涉及从理论到实践的不同层面。作者先详尽梳理了宋代论乐之作,包括单篇文章、诗话、词话、曲话中论乐的内容,以及宋代类书、史书、专著中涉及乐的内容等等,在文献梳理和观点提炼的基础上勾勒出了宋代乐论的理论发展脉络。在理论影响层面,作者强调乐论的“互动”性,即音乐观念对宋代文学思想的渗透和影响。例如,通过对“声诗”与“歌诗”的概念辨析,确证了“歌诗”一词在宋代的广泛使用,以及宋人“自觉将诗歌与音乐配合,而且也亲身用唱诗的方法实践之”(第197页)的事实。在实践层面,作者选取江西诗派为对象,通过对代表诗人诗歌格律特征的考察,论证了乐论的“形式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以“瓦子”为例,探讨了宋代俗乐兴起的现象,作为乐论发展和影响的一个参照。“瓦子”又称“瓦市”,“谓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吴自牧《梦梁录·瓦舍》)。这种隐形集市无疑是宋代市民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繁荣的产物,其文化意义在于:“单纯的政治空间受到了瓦子这一新兴的市民空间的巨大冲击,使得传统的物理空间开始具有了隐喻性和流动性,从而变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空间’或‘想象空间’。”(第161页)作者认为,“瓦子”的兴起为乐论在宋代的发展和改变提供了来自俗文化的张力。这种文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很好地弥补了文献研究和文本研究偏重于雅文化的不足,使研究更接地气,也展示出了宋代乐论发展和新变的现实土壤。
此外在研究结论上,该书提出了诸多具有洞见的观点,有利于对宋代乐论的重新认识和衡估。该书充分肯定了宋代在乐论研究史上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认为“宋代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在于它是传统音乐美学理论的经典化时期,也是最能体现雅俗文化对撞的时期,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也是传统乐论总结期和戏曲音乐的萌芽期,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第9页)。出于对宋代乐论特殊地位的充分认可,作者针对学界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异议。例如有学者曾指出:“由于礼教的束缚,由于宋明道学的禁锢,音乐美学思想却不仅囿于《乐记》而无重大突破与发展,而且变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陈腐。”(蔡忠德:《音乐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而作者反对这种“大而泛”的概括,认为“宋代乐论表面看来直接绍习先秦经典,但只不过将其作为一种理论的生发点,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乐论进行了历史的梳理和整合,即是说表面上似乎存在一种不合历史逻辑的断裂,实则是一种理性化的超越。”(第14页)作者是在充分占有材料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一论断,因此也更令人信服。此外,作者对于宋代乐论与文论之间关系的研究也颇具启示。作者写道:“宋代文论与乐论存在一种潜在的同构关系,如果说宋代是古代乐论的形式化时代,那么文论到宋代也经历了一个相似的过程,以苏轼开其端,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代表的江西诗派为中坚,以江西后学(吕本中、曾几)为尾声,这些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中都试图在遵从形式的基础上超越形式,并且以合乎自然声律为最高的形式理想,这恰与宋代乐论对‘音’、‘声’等形式因素的重视相得益彰。”(第10页)这一论断不仅凸显了宋代乐论的重要作用,也为我们理解宋代文论和文学创作提供了宏观视角的参照坐标。
当然该书仍存在一些不尽完善之处。例如,比较偏重乐论与诗的关系探讨,而对于其与词、戏曲等更加强调音律的文艺实践之间的关联,则未能充分展开。此外,对于音乐技术层面的问题如乐器、音律、音高、三分损益等,或许由于作者专业知识所限,也未能深入开掘。这些尚待解决的问题,为后继研究留下了启示和方向。
宗白华和汤用彤在探讨中国美学特殊性时指出,美学在西方是大哲学家思想体系中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史的内容,可以说是“哲学家的美学”;而中国的美学却纷杂地散布于各种艺术经验和艺术实践中,“中国古代的文论、画论、乐论里,有丰富的美学思想的资料,一些文人笔记和艺人的心得,虽则片言只语,也偶然可以发现精深的美学见解。”(宗白华,汤用彤:《漫话中国美学》,《光明日报》1961年8月19日版。)因此中国的美学更贴近“文艺美学”,只有具备区别于西方的思路、宽广的理论视野和踏实具体的研究对象,才能更深入地探寻中国美学的民族性特征和历史发展轨迹。在此意义上,《宋代乐论研究》的成绩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我们也期待学界更多成果的诞生和理论研究的进一步繁荣。

文心 诗情 博物 乐境
青少儿人文美育方案